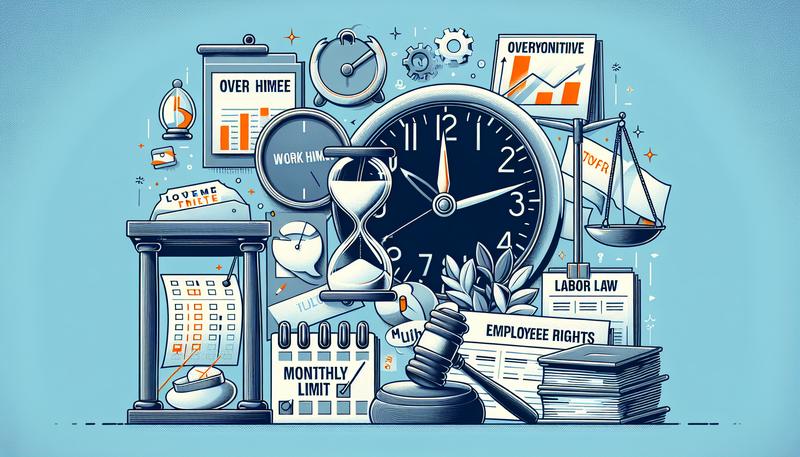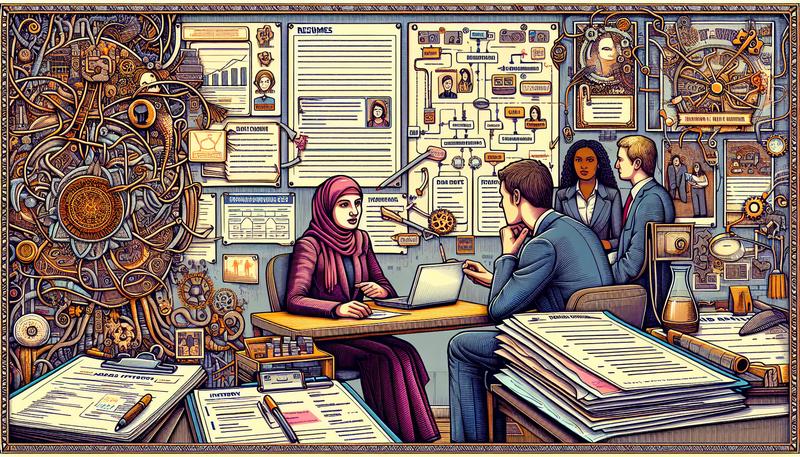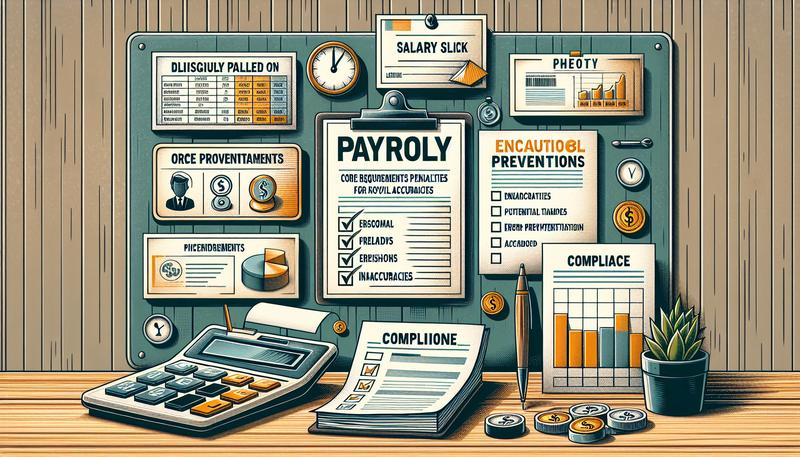在職場的語境中,「勞方」與「資方」是兩個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角色。我們通常直觀地將「資方」等同於「老闆」或「公司所有者」。然而,這個概念的內涵遠比表面看起來更為複雜。人力資源部門的同仁,是勞方還是資方?每日帶領團隊衝鋒陷陣的部門主管,又該歸屬於哪一方?當勞資雙方坐上會議桌,代表「資方」的究竟是誰?他們擁有什麼權力與責任?
本文將深入剖析「資方」這一角色,不僅從《勞動基準法》的嚴謹定義出發,更將結合勞資會議的實際運作、中高階管理者的角色困境,以及職場中的權力動態,為您描繪一幅完整、立體且深刻的「資方」圖像。
法律下的「資方」:不只是老闆一人
要理解「資方」,必須回到法律的源頭。根據我國《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的定義,雇主不僅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還包括了「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這句話的涵義至關重要,它明確地將「資方」的範疇從單一的企業主,擴展到了一個職能群體。任何在組織內被授權處理勞工相關事務的人,在法律上都可能被視為雇主的延伸,從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力資源(HR)部門。從法律角度看,人資人員擁有雙重身分:
- 身為勞方:他們和所有員工一樣,受雇于公司,付出勞務以換取薪資,其勞動契約受到公司人事制度的規範。
- 身為資方:他們代表雇主執行招聘、解僱、薪酬計算、出勤管理、勞健保投保等勞工事務,其職務行為在法律上等同於雇主的行為。因此,他們必須遵守勞基法中對雇主的各項義務要求。
同樣地,掌握著部門人事管理權(如績效考核、排班、准假等)的一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在其職權範圍內,也扮演著「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的角色。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八條中,會明確規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不得被選舉為「勞方」代表,因為他們在身份認定上更偏向資方。
勞資會議中的「資方代表」:權力與程序的體現
勞資會議是《勞動基準法》依據第83條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而設立的法定溝通平台。在這個平台上,「資方」的角色透過勞資會議勞資代表中的「資方代表」具體化。
誰能成為資方代表?
根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四條,資方代表由事業單位應就熟悉業務、勞工情形之人指派之。這意味著資方代表的產生並非透過選舉,而是由雇主直接任命。他們可以是公司負責人、股東、高階經理人或特定部門主管,其核心資格是了解公司營運與員工狀況以及事業場所勞工的情形。
資方代表的權力與會議的效力
勞資會議並非只是無關痛癢的談話會,它在法律上握有對特定勞動條件變更的「同意權」。許多企業經營所需的彈性措施,若沒有企業工會者,就必須經過勞資會議的決議才能合法實施。這凸顯了資方在會議中的關鍵角色。
以下是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必須經勞資會議同意(在事業單位無工會情況下)才能實施的重大事項,通常可透過下列方式議決:
| 事項 | 法源依據 | 內容簡述 |
| 二週變形工時 | 勞基法第30條第2項 | 將兩週內兩日的正常工時,分配到其他工作日。 |
| 八週變形工時 | 勞基法第30條第3項 | 將八週內的正常工時重新分配,以配合如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 |
| 四週變形工時 | 勞基法第30條之1 | 適用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的特定行業,提供更大的工時彈性。 |
| 延長工時(加班) | 勞基法第32條第1項 | 雇主必須先取得勞資會議同意,才能「具備」要求勞工加班的權利。 |
| 放寬加班時數上限 | 勞基法第32條第2項 | 在特定條件下,將每月加班上限從46小時提高至54小時。 |
| 輪班制更換班次休息時間 | 勞基法第34條第3項 | 在特定情況下,將輪班間隔從至少11小時縮短為不少於8小時。 |
| 例假調整(七休一例外) | 勞基法第36條第5項 | 在符合特定條件的行業中,勞工可連續工作超過6天。 |
此外,選派完成的勞資會議代表之名冊,事業單位必須在15日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這項程序要求確保了勞資會議的成立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規範。
現實的骨感:當「資方」遇上勞資會議
儘管法律對勞資會議有著詳盡的程序規定,但在現實操作中,其功能往往大打折扣,甚至淪為資方單方面意志的延伸。這種落差主要源於以下幾個結構性問題:
- 零監管的代表選舉與模糊的代表資格:勞方代表的選舉,辦法僅要求「公告」,而非「通知」到每一位勞工。這使得許多員工可能從未意識到大會選舉的存在。更關鍵的是,法規僅限制「一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不得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但「一級」的定義模糊,讓許多公司得以指派實際上更傾向管理層的「主管級」員工成為勞方代表,形成「資方代表」與「類資方代表」開會的局面。對於勞方代表資格與勞方候補代表的產生方式,若無嚴謹的內部監督,很容易遭到操控。
- 勞檢執法的選擇性寬容:根據勞工團體的觀察,勞動檢查機關對於「未給付加班費」的裁罰案件遠多於「未經勞資會議同意即要求加班」的案件。這顯示主管機關對於「加班」此一行為的程序正義(需經會議同意)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變相削弱了企業依法召開勞資會議的動機。對資方而言,只要事後補足加班費,程序上的違法風險相對較低。
- 無法撼動的會議表決結構:勞資會議的決議門檻極高,要求「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數之出席」,且勞資會議決議需「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由於資方代表由雇主指派,意見高度統一,他們只要集體反對或缺席,任何勞方想推動的議案都無法通過。反之,若資方想通過議案,只要能影響少數幾位勞方代表,便能輕易達到四分之三的門檻。此結構讓應選出代表總額中的資方代表實質掌握絕對優勢,即使勞方有遞補代表也難以改變局面。
因此,在缺乏強大勞工組織制衡的環境下,勞資會議中的「資方」往往掌握著絕對的主導權,會議很容易成為補全法律程序的形式,而非真正促進勞資合作事項,如改善工作效率事項的平台。
夾縫中的管理者:「我究竟是勞方還是資方?」
在法律定義與會議程序之外,「資方」更是一個存在於日常管理中的相對概念。對於廣大的中、高階管理者而言,他們是組織中最糾結、最矛盾的一群人,完美詮釋了「夾心餅乾」的處境。
兩種語言的翻譯者
管理者們發現,真正的資方(創辦人、董事會)與基層的勞方,說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
- 資方的語言:圍繞著「數字」打轉,包含KPI、業績成長率、用戶留- 存率、成本控制等。這些冰冷的數字是公司生存的命脈,是資方評估價值的核心標準。
- 勞方的語言:立足於「執行」的現實,充滿了用戶反饋、客戶抱怨、跨部門溝通的困難、做不完的工作等實際挑戰。
中高階管理者的核心任務,就是成為這兩種語言的翻譯者與緩衝帶。他們必須向上承接資方制定的「目標」與「壓力」,將其轉化為可執行的策略;同時,他們也必須向下理解勞方在執行時遇到的「挑戰」與「困難」,並向上反映,爭取資源。
尷尬的身份認同
這種角色定位帶來了巨大的身份認同困境。對老闆而言,管理者是必須為團隊成果負責的員工;對下屬而言,管理者卻是代表公司、執行命令的「老闆打手」。他們既不是純粹的勞方,因為他們需要為企業利益服務;也不是最終的資方, क्योंकि他們同樣面臨被考核、被要求甚至被解僱的風險。
成功的管理者,正是在這種資方理性與勞方感性的拉扯中,找到一條平衡的路。他們學習站在資方的角度去評估利弊,也學習站在勞方的立場去爭取支持,最終的目標是引導團隊(勞方)朝著公司設定的目的地(資方目標)前進,成為穩定企業前行的「導航」。
常見問題 (Q&A)
Q1. 人力資源(HR)部門算是勞方還是資方?
A: 在法律上,HR具有雙重身份。他們是公司的受僱員工,屬於「勞方」;但同時,他們又「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因此在法律上被視為雇主的延伸,需承擔「資方」的法律責任與義務。
Q2. 我們公司只有三個人,也需要有「資方代表」並召開勞資會議嗎?
A: 是的,仍須依法召開勞資會議。但根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二條,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人以下者勞雇雙方為勞資會議當然代表,可豁免許多正式的程序要求,例如勞方代表選舉、性別在事業場所勞工人數比例限制、任期規定以及向主管機關備查等。會議的召開與運作可以較為簡便。
Q3. 在勞資會議中,資方代表可以否決所有勞方提案嗎?
A: 實際上是的。由於會議決議需要「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而資方代表是由雇主指派,意見高度一致。只要資方代表集體不同意,任何勞方提出的議案都無法達到通過門檻。這種表決結構賦予了資方代表實質上的否決權。
Q4. 如果公司沒有召開勞資會議就讓我們加班,這樣合法嗎?
A: 不合法。根據《勞動基準法》第32條,雇主使勞工加班的「權利」,其前提是必須先經工會者,或在無工會的情況下經勞資會議同意。如果未履行此程序,即使個別勞工同意加班,公司在程序上仍然是違法的,可能面臨主管機關的罰鍰。不過,雇主依然必須依法給付勞工已提供的加班時數的加班費。
總結
「資方」從來不是一個單一、扁平的概念。它是法律條文中一個涵蓋廣泛的責任主體,是勞資會議中掌握程序與實質權力的指派代表,更是組織架構中承上啟下、充滿矛盾與拉扯的管理階層。
法律和制度的設計,初衷是為了平衡勞資雙方的權力,創造一個可以對話與合作的框架,謀求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然而,現實的勞資會議運作事項揭示了,在缺乏有效監督和勞方集體力量的制衡下,形式上的程序很容易被架空。
真正理解「資方」,意味著我們不僅要看見坐在權力頂端的企業主,也要看見那些在法律上被賦予雇主責任、在職場中扮演資方角色的各級管理者。唯有勞、資、管三方都能意識到各自的角色、責任與困境,才有可能在追求企業工作效率的同時,兼顧勞動者的公平與尊嚴,朝著真正的「勞資雙贏」邁出堅實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