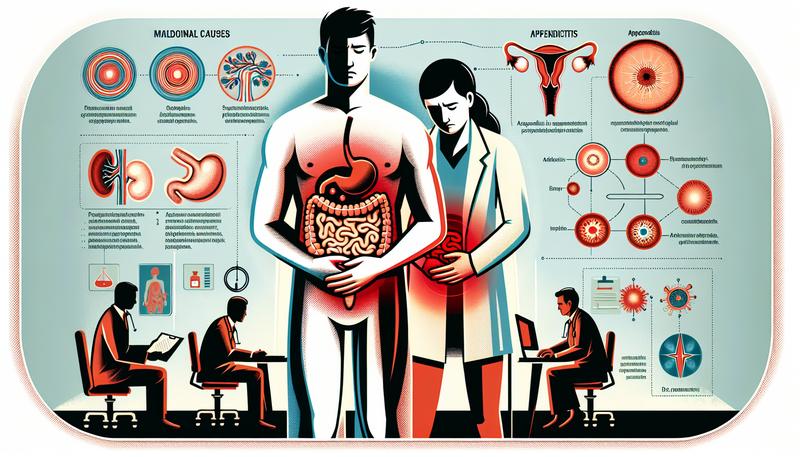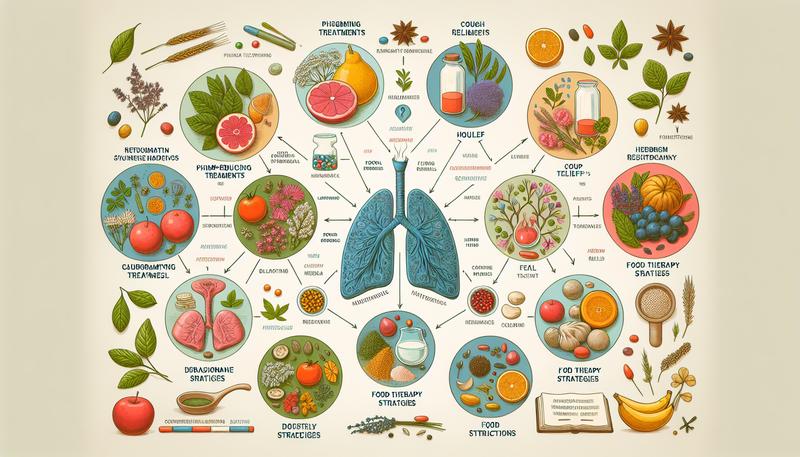當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角色應思聰因思覺失調症發作而被強制送醫時,這一幕不僅是戲劇高潮,更觸動了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公共安全與個人人權的敏感神經。
在現實生活中,無數家中正上演著類似的掙扎。當摯愛的家人因精神症狀影響認知功能而脫離現實,甚至出現自我傷害或傷人的風險時,照顧者往往陷入無助、恐懼與心力交瘁的困擾。「強制送醫」常被視為最後的手段,但它究竟是什麼?啟動的條件為何?從報案到入院,又會經歷哪些複雜的流程與挑戰?
本文將整合法律規範、第一線人員的實務經驗及人權觀點,詳細拆解「強制送醫」與「強制住院」的每一個環節,為徬徨中的家屬、第一線工作者及關心此議題的社會民眾,提供一份清晰、完整的指南。
第一階段:啟動「緊急護送就醫」— 條件、流程與挑戰
大眾口中的「強制送醫」,在法律上的正式名稱為「緊急護送就醫」。這並非家屬單方面要求即可啟動,而是有著嚴格的法律要件與執行程序,旨在平衡精神病人人權與公共安全。
法律要件:不僅是「感覺」,更需「事實」
根據《精神衛生法》的規定,啟動緊急護送就醫的核心要件是,精神疾病當事人需處於「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的狀態。這句話看似簡單,但在實務執行上卻極為嚴苛。
現在進行式: 當事人正在做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例如持刀、攻擊、以頭撞牆等。這是最明確、最無爭議的啟動條件。
未來式(之虞): 這是指當事人有極高的風險即將造成傷害。然而,「之虞」的判斷並非憑藉家屬的「感覺」或「猜測」,而是需要具體證據支持的行動或計畫。例如:
- 風險不足: 僅僅口頭嚷著「我想死」或「我要殺人」。
- 風險可能成立: 除了言語表達,還伴隨實際行動,如在短時間內大量購買刀械並揚言殺人、購買木炭並透露出自殺計畫、或已站上頂樓陽台等。
執行流程與各單位角色
一旦情況符合緊急護送的要件,家屬可撥打 110 或 119 求助。此時,一場多方協作的救援行動將展開,各單位分工如下,各司其權責:
| 單位 | 核心任務 | 具體工作內容 |
|---|---|---|
| 警察機關 (110) | 維持現場秩序、排除立即危險 | 1. 評估現場安全,制止暴力或危險的他人行為。 2. 協助查明當事人身分。 3. 在護送過程中提供戒護,確保人員安全。 4. 依規定全程錄影音存證。 |
| 消防單位 (119) | 醫療救護、護送 | 1. 消防人員評估當事人的生命徵象與身體狀況。 2. 若有外傷,進行初步急救。 3. 提供安全的運輸工具(救護車),將當事人護送至精神醫療機構。 |
| 衛生單位(地方主管機關) | 專業評估、資源連結 | 1. 由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或公共衛生護理師進行精神狀況評估。 2. 確認當事人是否為已列管追蹤的個案。 3. 若無法到場,可透過視訊等科技設備提供專業意見。 4. 協助家屬聯繫醫院,並在事後安排社區追蹤關懷。 |
家屬面臨的實務挑戰
正如一位家暴社工所言,強制送醫是一門「學問」。家屬在處理這類案件的過程中常會遇到以下困境:
- 「一秒變正常」的窘境: 許多精神病患在看見警察、消防員等穿制服的人員到場後,會因情境轉變而暫時恢復平靜或躲藏起來,導致第一線人員因未目睹危險行為而無法介入。
- 證據的重要性: 為應對上述情況,聰明的家屬會學習在衝突當下,用手機錄影存證。這段影片能向執法人員證明,病患確實存在與現實脫節的言行,而不僅是一般的家庭口角。
- 家庭共識的缺乏: 若家庭成員對是否送醫意見不一(例如,姊姊主張送醫,父母卻反對),將使第一線人員陷入兩難,擔心事後被控告妨礙自由,從而降低介入意願。因此,在求助前,取得家庭內部共識至關重要。
第二階段:從「送醫」到「住院」— 醫院端的專業鑑定
成功將家人護送到醫院急診室,僅僅是完成了第一步。「緊急護送就醫」不等於「強制住院」。能否讓病患接受住院治療,取決於醫院端更為嚴謹的第二階段評估。
強制住院的嚴格門檻
在急診室,當事人會先接受身體檢查,並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進行會診。醫師的評估核心在於判斷是否因疾病影響而符合《精神衛生法》中「強制住院」的兩大要件:
- 診斷為「嚴重病人」: 根據法律定義,「嚴重病人」是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醫療診斷認定者」。這需要醫師的專業判斷。
- 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 即使診斷為嚴重病人,還必須評估其傷害自己或他人的風險是否高到「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且病人本人因缺乏病識感而仍然拒絕接受治療。
審查與權利保障
若醫師認為符合上述所有情形,流程將進一步升級:
- 雙重鑑定: 需由兩位以上的指定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確認住院的必要性。
- 審查會許可: 醫療機構必須將鑑定結果、相關診斷證明及病患與保護人的意見,送交衛生福利部的「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進行審查。唯有獲得審查會許可,強制住院才合法。
- 住院期限: 強制住院期間不得超過60天。若需延長,必須再次經由醫師鑑定和審查會許可,每次延長同樣以60天為限。
- 病患權利: 在此期間,病患或其保護人有權向法院聲請提審,要求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家屬的角色:從求助者到資訊提供者
面對僅有短短幾十分鐘評估時間的醫師,家屬的角色至關重要。醫師不認識你的家人,也無法僅憑家屬的口述就做出剝奪人身自由的重大決定。此時,家屬應避免與病人辯論事情的真假,而是主動提供具體事證,例如:
- 播放衝突影片: 直接讓醫師看到病患在日常生活中失控的樣貌。
- 提供行為紀錄: 整理出病患近期異常言行的時間軸與具體事件。
- 說明對生活的影響: 具體描述病患的精神病症狀如何導致他「無法處理自己事務」。
人權的拉扯:強制住院的爭議與未來
強制住院制度,本質上是在「個人自由」與「社會安全」之間尋求平衡,但這條鋼索極難行走。
人權觀點的挑戰: 2017年,台灣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國際審查中,被指出強制住院制度可能違反公約精神,即「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人權團體倡議,應發展以人為本、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系統,而非僅僅依賴強制性的就醫機制。
照顧者的沉痛呼告: 然而,對於長年孤軍奮戰的家屬而言,強制住院是他們在耗盡所有心力後,唯一能暫時喘息的防線。他們憂心,若在沒有充足社區配套資源的情況下貿然廢除此制度,無異於將他們推入更深的絕望。這凸顯了國家將照顧責任過度轉嫁給家庭,許多家庭在求助精神醫療之前,可能已先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尋求民間信仰的協助,卻未提供相應支持的結構性問題。
尋找更好的解方—美國「降落傘計畫」的啟示: 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提到,美國的「降落傘計畫」是一個值得借鏡的模式。它提供一個自願性的、臨時性的社區居住環境,讓處於危機中的精障者可以短暫入住。在這裡,他們能獲得同儕支持,同時保有工作、就學與通訊的自由,不像被送進精神病院般與世隔絕。這個計畫不僅給予精神病患者本人支持,也為照顧者創造了喘息空間,並有專業團隊介入,分別協助雙方。
常見問題 (FAQ)
Q1: 強制送醫和強制住院有什麼不同?
A1: 這是兩個不同階段的概念。「強制送醫」是指在當事人有自傷傷人之虞時,由警消、衛生單位等將其護送至醫院急診的過程,法律上稱為「緊急護送就醫」。而「強制住院」則是在醫院內,經過兩位以上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由審查會許可後,才能執行的全日住院治療,其門檻遠高於強制送醫。
Q2: 家人出現精神症狀但沒有暴力行為,也不肯就醫,我該怎麼辦?
A2: 根據多家發布單位如衛生局的建議,在沒有立即危險性的前提下,應優先採用柔性勸導。可以「動之以情」,站在對方立場,從其身體不適(如已經好多天睡不好、心悸)切入,建議去看診改善症狀。也可以「說之以理」,解釋這些狀況可能源自大腦這個身體器官的問題,例如「自律神經失調」或「血清素分泌不足」,用去標籤化的詞語降低其對精神科的負面觀感,並以身體的不舒服作為引線,引導就醫。
Q3: 警察來了,病人卻突然變正常,他們不肯處理怎麼辦?
A3: 這是常見的困境。最好的應對方式是「事前存證」。在病人發作、出現怪異言行時,用手機錄下影像。這段客觀的證據可以幫助第一線人員了解平時的狀況,避免因當下情況的不明朗而無法處理。
Q4: 病人被強制住院後,家屬的責任就結束了嗎?
A4: 沒有。住院是短期治療,家屬與親友仍需扮演關鍵角色。應配合醫院的治療計畫,參與家庭會議,提供病患的日常資訊,並為病患出院後的回歸社區生活做好準備。出院後的穩定服藥與社區追蹤,更是防止復發的重要環節。
Q5: 強制住院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嗎?有沒有其他選擇?
A5: 強制住院是危機處理的最後手段,而非唯一解方。理想的模式是發展多元的社區支持系統,例如提供臨時居住空間、同儕支持、日間照顧中心、社區關懷訪視員等,讓病患在社區中就能獲得足夠的支持,從而減少需要強制住院的危機情況。
總結
「強制送醫」是一項粗糙且不完整的解方,誠如廖福源所喻,它僅是「讓溺水的人暫時不會溺水」,卻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它是一個複雜、多階段、高門檻的法律程序,牽動著病患、家屬、醫療人員與社會安全等多方利益。
理解其運作的細節,有助於我們在危機發生時做出更正確的判斷。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超越「送醫與否」的二元對立,共同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這包括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發展多元的社區支持服務(如降落傘計畫)、給予家庭照顧者實質的資源與喘息服務,並從教育著手,減少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接住每一個在困境中掙扎的靈魂,讓「與惡的距離」不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