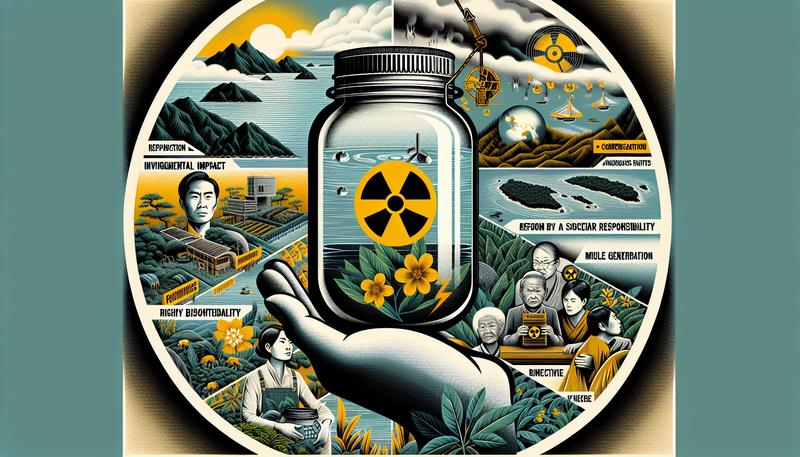在台灣東南方的太平洋上,有一座名為蘭嶼島的蔥鬱火山島,它是達悟族(雅美族)人世代相傳的家園。然而,自1982年起,這座「人之島」被迫承擔起台灣核能發展背後最沉重的代價。
超過十萬桶低放射性核廢料,在一個充滿爭議與欺瞞的開端後,被運至此地「暫存」。四十年過去了,這份「暫時」的負擔,已演變成一場牽涉政府失信、原住民權益、環境正義與世代對立的複雜核廢問題。本文將深入剖析蘭嶼核廢料爭議的始末,探討其歷史脈絡、抗爭歷程,以及至今仍未解的遷場難題。
謊言與真相——「罐頭工廠」的誕生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的歷史,始於一個對當地居民的系統性欺瞞。1970年代,台灣威權政府為了解決國內核電廠、醫療、工業及研究機構產生的低放射性廢棄物,開始尋找處置地點。當時,經行政院核准,政府的專家學者在與台灣省政府協調後,評估了廢棄礦坑、高山、無人島等多種方案,最終選定了蘭嶼南端的蘭嶼龍門地區。
政府向行政院陳報的理由是,該地三面環山、一面向海,地形封閉,且五公里內無居民,加上符合投資效益,適合做為「暫時貯存」的地點。最初的計畫是,將核廢料暫放於此,待日後技術成熟時,再進行「海洋投棄」,也就是將廢料桶拋入深海。
然而,在建設過程中,政府並未與達悟族人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溝通或取得其同意。島上謠言四起,有人說是蓋「鳳梨罐頭工廠」,也有人說是「魚罐頭工廠」。當地居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以為新的建設能帶來就業機會。直到1980年,一位名叫董森永(Syapen Lamoran)的牧師從報紙的一篇不起眼報導中,才揭開了這個驚人真相——這座大型工地,竟是國家級的核廢料貯存場。
儘管政府事後澄清,其官網說明及官方文件中從未使用「罐頭工廠」一詞,但對達悟族人而言,「被欺騙」的感受已深植人心。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隨著國際社會環保意識抬頭,1996年《倫敦公約》全面禁止核廢料的海洋投棄,使得蘭嶼這個「中繼站」的計畫徹底破滅,所謂的「暫存」變成了遙遙無期的「永久」存放。
鏽蝕的惡靈——核廢料的威脅與達悟之怒
蘭嶼貯存場自1982年啟用,至1996年貯滿關閉,共接收了97,672桶來自全台各地的低放射性廢棄物。這些廢棄物主要是受放射性污染的工作服、手套、廢樹脂、濃縮廢液等,與核電廠反應爐內用過、需在燃料池中長期冷卻的高放射性燃料棒不同,經水泥或柏油固化後封存於55加侖的鋼桶內。
蘭嶼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數量來源統計 (如下圖所示)
| 來源單位 | 原始貯存桶數 | 備註 |
|---|---|---|
| 核一廠 | 40,326 | 部分廢棄物桶經破碎重新固化後,體積增加。 |
| 核二廠 | 29,198 | |
| 核三廠 | 11,832 | |
| 核能研究所(核研) | 4,960 | |
| 全國醫、農、工、學術研究等 | 11,292 | |
| 檢整重裝固化桶 | 64 | 早期桶身鏽蝕後,重新處理分裝產生。 |
| 總計 | 97,672 | 經檢整重裝後,目前總桶數增加為100,277桶。 |
蘭嶼高溫、潮濕、多鹽分的氣候,對這些鋼桶是嚴峻的考驗。1994年,外界震驚地發現,許多貯存超過十年的核廢料桶已嚴重鏽蝕、破損,甚至變形。根據中央社報導,2024年監察院的實地履勘再次證實,許多桶身銹腐、膨脹、位移推擠的問題依然存在,對環境構成了潛在威脅。
對達悟人而言,這些鏽蝕的鐵桶如同「惡靈」,不僅帶來對癌症罹患率上升、漁獲變異的恐懼,更侵犯了他們賴以維生的土地。儘管台電公司與核安會多次引用科學研究,聲稱輻射影響「微乎其微」,但一份2011年中研院的報告(即輻射外洩事件)卻指出,貯存場出海口的藻類沉積物中,檢測到人工核種鈷-60和銫-137,且輻射數值高於核三廠,加深了族人的不信任。
真相大白與環境威脅點燃了達悟族人的怒火。自1988年起,他們發起了數次大規模的「220反核廢、驅逐惡靈」運動。抗議者衝擊核廢設施、並前往台北在鄉公所前靜坐,更在1995年發動「一人一石填港行動」,以巨石封鎖港口,成功阻止了後續核廢料的運入。
世代的傳承——從街頭到網路的持續抗爭
蘭嶼的反核廢運動,展現了清晰的世代交替軌跡。
- 第一代抗爭者:以董森永牧師、郭健平(Shaman Fengayan)等人為代表,他們在資訊封閉的年代,勇敢地挑戰威權體制,奠定了抗爭的基礎。
- 中生代的接棒:隨著前輩年事已高,像魯邁(Luman)這樣的反核中生代,感受到接棒的責任。他們成長於「與核廢料共存」的環境,承先啟後,連結著不同部落世代的抗爭能量。
- 青年的新模式: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以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希婻.瑪飛洑(Syaman Macinanao)為首的年輕一代,為反核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成立「蘭嶼青年行動聯盟」,善用臉書等社群網路串連,發起如「核廢場前靜坐跨年」等創意抗議,並結合淨灘、文化推廣等活動,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守護家園。
然而,並非所有年輕人都對此抱持同樣的熱情。隨著觀光業成為蘭嶼的經濟支柱,一些年輕人認為,「反核」已是陳腔濫調,他們更願意將精力投入在撿拾垃圾、推廣達悟文化等更為實際的議題上。這種分歧,也反映了蘭嶼社會在長期抗爭後的疲憊與轉變。
失信的政府——補償、道歉與遷場僵局
面對達悟族人長年的抗爭,政府的應對措施始終充滿爭議。
- 承諾跳票:政府曾承諾在2002年前將核廢料遷出蘭嶼,但此承諾最終跳票,引發全島罷工罷課,嚴重侵蝕了政府的公信力。
- 真相調查與道歉:2016年,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承認當年未經達悟族人同意便興建貯存場。隨後的真相調查報告也確認了此一歷史錯誤。
- 金錢補償:政府提出給予蘭嶼25.5億新台幣的「回溯性補償金」,並每三年支付額外款項。然而,此舉被許多反核人士視為用錢收買的「糖果」,意圖平息民怨、削弱抗爭力道,但也有部分居民選擇接受。
- 遷場遙遙無期:遷場是蘭嶼議題的核心,卻也是最無解的難題。經濟部督導的台電公司曾將台東達仁、金門烏坵列為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建議場地點,但因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強烈反對,連公投都無法舉行。對照核一、核二廠乾貯設施因新北市政府的安全疑慮而延宕,凸顯了核廢設施選址的普遍困境。由於遲遲找不到最終處置場址,台電甚至在2024年因此被原能會(現核安會)開罰1000萬元。
目前,台灣所有核廢料(包含高階與低階)都尚無最終處置場,甚至連相關的選址條例都立法不全。核廢料已成為全台避之唯恐不及的「鄰避設施」,在沒有任何縣市願意接收的情況下,蘭嶼的十萬桶核廢料,只能繼續留在原地。
常見問題 (FAQ)
Q1: 蘭嶼的核廢料是什麼?對人體有立即危險嗎?
A: 蘭嶼存放的是「低放射性廢棄物」,主要來自核電廠運轉及醫、農、工等領域產生的受污染物品。其輻射強度遠低於核電廠用過的高階核燃料棒。官方稱其對環境影響極微,但由於存放已久,許多桶身鏽蝕破損,引發輻射外洩的疑慮與爭議,對居民造成長期的心理壓力與不信任感。
Q2: 政府當初為何選擇在蘭嶼興建貯存場?
A: 1970年代,政府認為蘭嶼地處偏遠、居民稀少,且原始計畫是將其作為核廢料「海洋投棄」前的「暫時」存放點,也就是一個廢棄物貯存設施。然而,此決策過程並未徵求當地達悟族人的同意。
Q3: 核廢料至今仍無法遷出蘭嶼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A: 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國際公約已禁止將核廢料拋入海洋,使得最初的計畫不可行。第二,台灣至今未能找到任何一個縣市願意接納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或集中式貯存場,這是典型的「鄰避效應」(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導致遷場計畫完全停滯。
Q4: 所有達悟族人都反對核廢料嗎?
A: 絕大多數達悟族人都希望核廢料能盡快遷出蘭嶼。但隨著時間推移,不同世代的抗爭方式與生活重心有所不同。部分年輕人更關注觀光發展與文化傳承,而政府的補償金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內部不同的聲音,但要求「核廢遷出」仍是跨世代的主流共識。
Q5: 台灣的核廢料問題最終有解決方案嗎?
A: 理論上的解決方案是興建「最終處置場」,將高階核廢料深埋在地底,低階核廢料則置於地表或淺層的工程設施中。然而,從選址、社會溝通到立法,每一步都極其困難。目前芬蘭是全球唯一建成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國家。台灣的核廢料處理進程嚴重落後,在達成社會共識與找到合適場址之前,恐怕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總結
蘭嶼核廢料爭議,遠非單純的環保或能源議題。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原住民族權益的踐踏與對程序正義的漠視。從最初的欺騙,到後來的承諾跳票,再到今日無解的遷場僵局,蘭嶼的傷痛是整個台灣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歷史共業。
無論未來台灣的能源政策走向擁核或非核,已經產生的核廢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如何以負責任的態度,透過公開、透明的社會溝通,並在符合環境正義的前提下,為這些核廢料找到一個永久、安全的家,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對蘭嶼達悟族人遲來的正義,以及對台灣這片土地未來世代的承諾。在找到最終解方之前,蘭嶼的這道傷痕,將持續提醒著我們這段不應被遺忘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