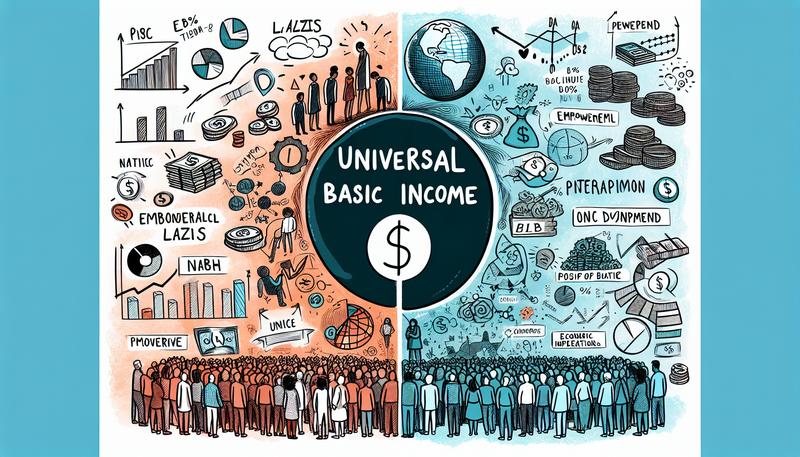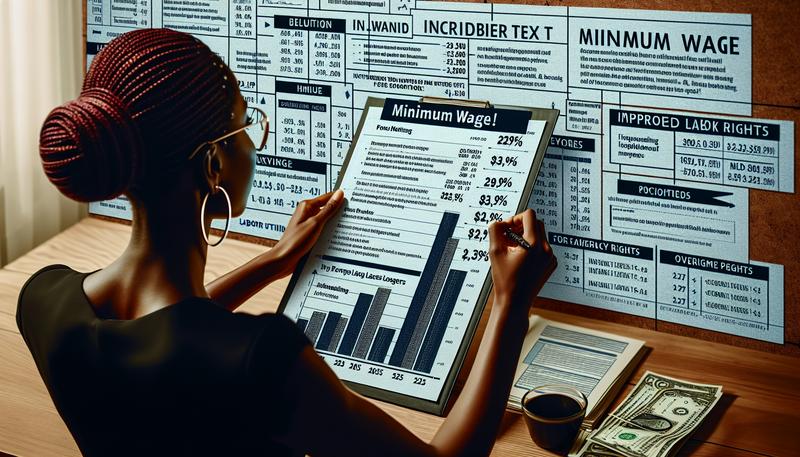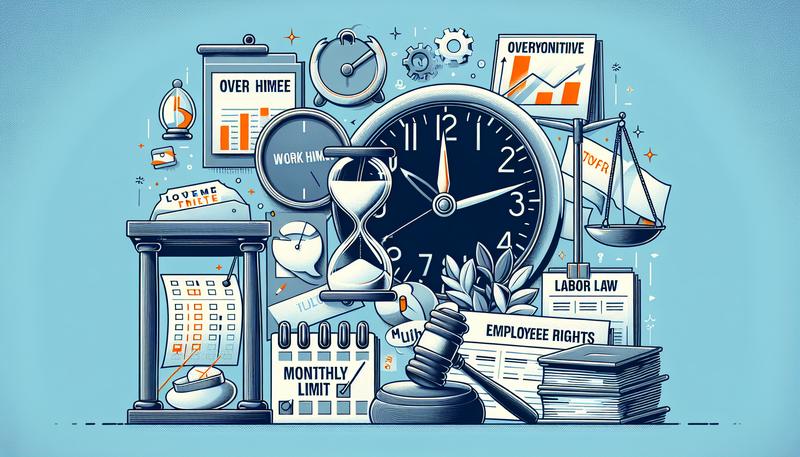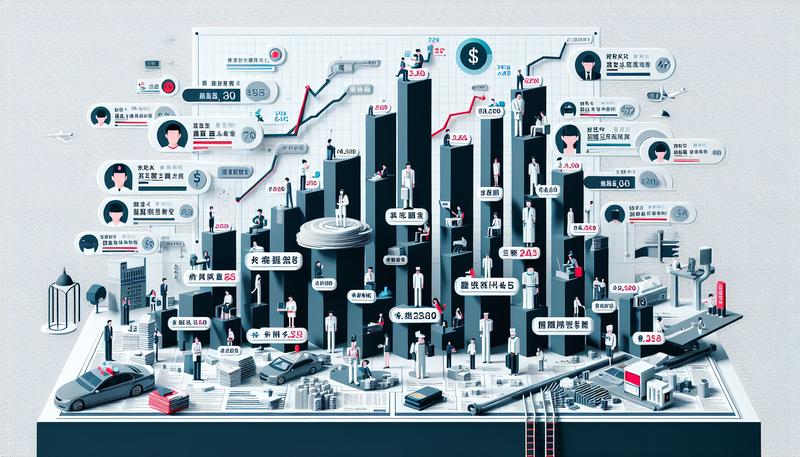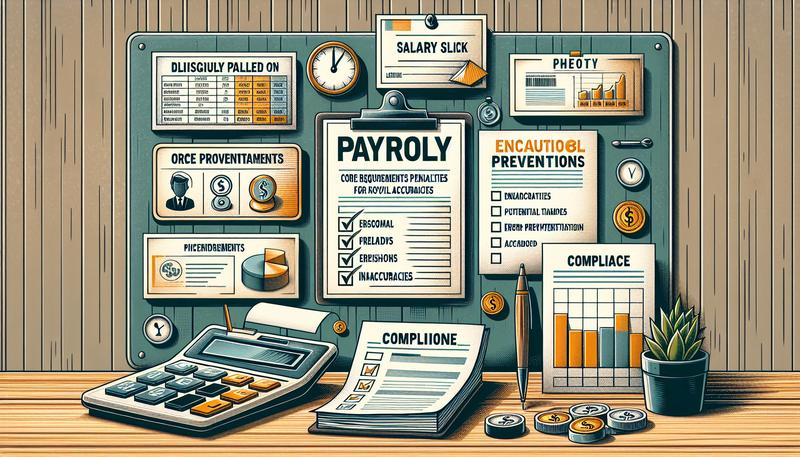隨著人工智慧(AI)與机器人的飛速發展,從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到華裔政治家楊安澤(Andrew Yang),世界各地的思想領袖與實踐者,都不斷拋出一個深刻的省思:「當機器與演算法能勝任多數人類工作時,我們的社會該如何維繫?人人又該如何維生?」在這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時代背景下,「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這個看似激進的構想,正從學術殿堂與烏托邦的想像中走出,成為全球多國認真探討、甚至小規模試驗的社會政策。
本文旨在深度剖析UBI的完整面貌與內容,不僅僅是「發錢」的簡單概念。我們將從其核心定義與歷史脈絡出發,系統性地盤點全球各地的關鍵實驗及其結果,深入探討支持與反對雙方的核心論點,並最終聚焦於台灣本土的倡議、實驗與社會反響,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且細緻的思考框架,探討其提升社會整體韌性的可能性。
什麼是無條件基本收入?——超越傳統福利的五大核心原則
無條件基本收入(又稱全民基本收入UBI),並非傳統的社會救濟或失業補助。它具備五個不可或缺的核心原則,使其與現行社福制度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 定期發放(Periodic): 它不是一次性的紓困金或消費券,而是以可預期的週期(例如每月)持續發放,提供穩定的經濟基礎。
- 現金支付(Cash Payment): 直接發放金錢,而非食物券或特定服務,賦予個人最大的自主權,可以根據自身最迫切的需求進行支配,是一種有效的現金補助。
- 以個人為主體(Individual): 發放對象是每個獨立的個人,而非家庭或組織,這有助於保障家庭成員(特別是女性)的經濟獨立性與家庭關係。
- 普遍性(Universal): 發放給所有公民或地區所有居民,無論其貧富、職業或身分,不進行排富或資格審查。
- 無條件(Unconditional): 領取者不需滿足任何工作、求職、接受特定訓練或從事勞務的附加條件。
世界銀行的理論架構將社會福利政策置於三個維度:支付目標(全民或特定群體)、支付條件(無條件或有條件)與支付方式(現金或實物)。 UBI正是這三個維度中最極端的組合:對全民、無條件地、支付現金。簡單來說,基本收入就是保障每個人基本生活條件的社會制度。
這種設計的初衷,正是為了解決傳統福利政策的根本性難題:如影隨形的「標籤化效應」、「貧窮陷阱」與行政官僚問題。現行製度為了「精準」鎖定補助對象,需要耗費龐大的行政成本進行資格審查,需要動用大量人力、設備來處理繁瑣的資料,而受助者也常因被貼上「低收入戶」或「失業者」的標籤而承受心理壓力和社會污名。
更甚者,當找到一份僅略高於補助門檻的工作時,便會失去所有補助,反而削弱了其脫離貧困的動力。 UBI的支持者認為,透過「普遍」且「無條件」的設計,能徹底根除這些弊端,確保援助能觸及所有需要的人。
UBI的緣起與演進:從烏托邦到AI時代的應對之策
UBI並非橫空出世的新概念,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數百年前。
- 文藝復興的萌芽: 1516年,英國思想家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在其著作《烏托邦》(Utopia)中,便提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所需,以根除犯罪的思想雛形。其友人、學者喬漢尼斯·維夫斯(Juan Luis Vives)則進一步規劃了由市政當局為窮人提供最低生活支持的務實計畫。
- 啟蒙時代的倡議: 美國開國元勛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在《耕地正義》中明確主張,國家應定期向國民發放「自然繼承」的紅利,作為對其共享自然資源的補償。
- 20世紀的發展: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倡導保障維生的「基本所得」。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提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的構想,雖有條件限制,但已具備UBI的分配精神。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也曾呼籲實施「有保障的所得」。
然而,真正將UBI推向全球政策前線的,是當代「技術性失業」的迫切威脅。牛津大學2013年的研究預測,未來10至20年,美國高達47%的工作有被AI與自動化取代的風險。
當創造新工作的速度遠不及舊工作消失的速度時,社會將如何分配由機器創造的巨大財富? UBI被視為一種可能的解方,確保即使在勞動需求大幅下降的未來,每個人仍能分享科技進步的果實,並擁有基本的生活尊嚴。
全球實驗大盤點: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近年來,世界各地展開了規模與形式各異的UBI實驗,其結果挑戰了許多刻板印象,也揭示了現實的複雜性。這些基本收入實驗的資料,為後續的政策討論提供了寶貴依據。
| 國家/地區 | 計畫名稱/地點 | 期間 | 核心特徵 | 主要發現與結果 |
|---|---|---|---|---|
| 美國(阿拉斯加州) |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 (Alaska Permanent Fund) | 1982年至今 | 每年發放石油收益分紅,金額不固定。 | 長期實施,對就業影響極微,並有助於降低貧困率。 |
| 加拿大(多芬市) | 米糠計畫 (Mincome) | 1974-1979 | 對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收入,有遞減機制。 | 顯著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狀況(住院率下降)、提升了青少年的教育完成率。工作時數僅微幅下降。 |
| 芬蘭 | 全國性實驗 | 2017-2018 | 隨機挑選2,000名失業者,每月發放560歐元。 | 相較於對照組,實驗組的心理健康、幸福感與信任度顯著提升。對就業率的提升效果不明顯,但實驗結束後,芬蘭政府未繼續推行。 |
| 印度(中央邦) | SEWA/UNICEF計畫 | 2011-2012 | 對8個村莊的居民發放小額基本收入。 | 居民的營養、健康與衛生狀況顯著改善,兒童就學率提高,也催生了許多小型創業活動。 |
| 肯亞 | GiveDirectly 計畫 | 2016年至今 | 長期(最長12年)向貧困村莊居民發放現金。 | 整體勞動力供應未見下降,但許多人從受薪工作轉為自營生意,促進了地方經濟與女性賦權。 |
| 德國 | 我的基本收入 (Mein Grundeinkommen) | 2021-2024 | 非營利組織資助122人,每月領取1,200歐元。 | 參與者並未減少工作意願,反而回報更高的工作滿意度、更低的壓力水平,並將更多時間用於進修與志工服務。 |
| 瑞士 | 全國性公投 | 2016年 | 提案將UBI入憲,每月約2,500瑞士法郎。 | 公投以76.9%的高比例被否決。主要擔憂來自於高昂的財政成本、對工作倫理的衝擊,以及可能吸引大量移民。 |
從這些實驗結果中可以觀察到,UBI的影響是多面向的。在低收入國家,它在改善基礎生活條件、健康、教育與促進創業方面效果顯著。在高收入國家,其影響則更多體現在提升心理健康、賦予勞工更多選擇權與轉職的勇氣。關於「UBI會讓人變懶」的普遍擔憂,在多數實驗中並未得到證實。
UBI的論辯:支持與反對的激烈交鋒
圍繞UBI的討論,始終存在著壁壘分明的兩派觀點。
支持方的核心論點:
- 降低貧富差距與提振內需: UBI作為一種財富的再分配機制,雖是齊頭式發放,但對窮人的邊際效益遠大於富人,能有效縮小貧富鴻溝。同時,提高底層民眾的消費能力,能刺激內需市場,活絡經濟。
- 賦予勞工真正的自由與尊嚴: 當人們無需為基本生存而被迫接受惡劣、低薪工作時,企業將有更大壓力改善勞動條件。勞工也更有底氣去追求符合志趣的工作,或投入時間進修,這對現代人人生規劃至關重要。
- 認可無償工作的價值: 社會中有大量對人類福祉至關重要的無償工作,如育兒、照顧長者、家務勞動、社區志工、開源軟體開發等。UBI是對這些貢獻者最直接的經濟認可與支持,也能讓人們有餘裕參與社會運動。
- 促進性別平等與社會穩定: UBI賦予每個人獨立的經濟來源,有助於打破家庭中因經濟依賴而產生的權力不對等,特別能提升女性的自主性。此外,透過提供經濟安全感,可望降低因貧窮衍生的犯罪率與社會成本。
- 適應未來經濟模式: 在零工經濟(gig economy)與短期合約日益普遍的時代,UBI能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讓人們在不同工作間轉換時無後顧之憂。
反對方的核心質疑:
- 財政的可行性: 這是最現實的挑戰。錢從哪裡來?若要實現有意義的UBI,可能需要大幅提高稅收(如所得稅、消費稅、碳稅、財富稅)或削減現有公共支出,其政治阻力與經濟影響難以估計。
- 摧毀工作誘因: 儘管實驗數據多不支持此論點,但反對者仍擔心,大規模、永久性的universal basic income會侵蝕社會的勞動倫理,導致勞動力供給下降,最終拖垮整體經濟。
- 通膨風險: 若總供給不變,全民增加的購買力可能導致物價全面上漲,從而抵銷UBI的效益。伊朗2011年現金發放計畫的後期,就因未隨通膨調整金額而使民眾實際購買力下降。
- 「昂貴但又不夠慷慨」的兩難: 為了財政可行,UBI的金額可能設定得較低,不足以讓赤貧者脫困。但若它取代了現有針對重度弱勢群體(如殘障人士)的更高額補助,反而會傷害到最需要幫助的人。這種情況將是一大挑戰。
聚焦台灣:從倡議到在地實驗
在台灣,UBI的討論也逐漸升溫。非政府组织「UBI Taiwan 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自2017年起便積極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政策白皮書、在facebook等平台進行倡議,乃至2020年的遊行活動,在公共領域播下種子。
2020年,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出現相關提案,但最終未獲通過,反映了當時官方的保守態度。然而,民間的探索並未停止。2023年,UBI Taiwan啟動了台灣首個UBI實驗計畫,其意義非凡。
該計畫鎖定了一位因資格限制而難以獲得政府穩定金援的單親媽媽(于媽媽),在為期一年的時間裡,每月為她提供新台幣一萬元的無條件現金支持。這個實驗雖是個案,卻揭示了深刻的質化意義:這筆收入不僅改善了她與孩子的生活品質與關係,更重要的是,在後來她被診斷出癌症時,成為了支撐她度過難關、穩定家庭的關鍵力量,凸顯了現行社福在應對突發危機與生活壓力時的不足。
此外,根據《風傳媒》的網路民調,有近六成民眾對每月1.5萬元的UBI表示贊成,其中超過七成的贊成者表示會繼續現在的工作或轉換到更喜歡的工作,僅有少數人會選擇完全不工作。這顯示台灣社會對於工作的人的想法,以及對UBI的接受度與工作倫理的看法,或許比想像中更為開放。
常見問題(FAQ)
Q1: UBI不就是共產主義嗎?
A1: 不是。兩者有根本性不同。共產主義的核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並強調「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常導致個人工作動機被削弱。而UBI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下運作,它不取消私有財產,也不干預市場定價。它旨在消除「不工作就會餓死」的負向懲罰,但保留了「更努力工作能過上更好生活」的正向激勵,人們依然可以透過工作賺取遠高於基本收入的財富。
Q2: 全民發錢不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嗎?
A2: 這是一個重要的顧慮,但多數研究顯示其影響有限。在市場機制健全的經濟體中,增加的需求也會刺激供給提升。此外,資金可以來自於對高污染、高耗能產業或財富的課稅,本身就帶有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真正的通膨風險,更可能來自於計畫設計不當,例如發放的金額未與經濟增長掛鉤,或在供給鏈脆弱的國家實施,如伊朗的案例所示。
Q3: 實施UBI的錢到底從哪裡來?
A3: 這是UBI面臨的最大挑戰。全球討論的財源方案主要有幾大類:
- 整合與節流: 整合現有的、繁雜的社會福利與補貼,並節省其龐大的行政審查成本。
- 調整稅制: 提高或開徵新稅,例如提高消費稅(VAT)、開徵碳稅或環境稅、對金融交易課稅、向自動化與AI的持有者(例如科技公司)課徵「機器人稅」、或大幅提高遺產稅與資本利得稅等財富稅。
- 分享公共紅利: 將屬於全民的自然資源(如阿拉斯加的石油)或公共創造的價值(如數據)所產生的收益,以分紅形式發放給全民。
Q4: 為什麼要發錢給所有人,包括郭台銘那樣的富人?這樣不是很浪費嗎?
A4: 這是「普遍性」原則的核心精神,其目的有三:
- 消除污名與保障尊嚴: 當每個人都能領取時,就沒有人会因為領取而被標籤化。
- 降低行政成本: 省去了辨識誰是「窮人」、審查資格的巨大行政開銷與繁複程序,避免資源浪費在官僚體系中。
- 確保完全覆蓋: 任何資格審查制度都存在「漏網之魚」,總會有一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因為信息落差、程序複雜或不願被標籤而無法獲得援助。普遍發放能確保100%覆蓋。此外,富人領到的基本收入,可以透過累進稅制等方式,再從其總收入中課徵回來,實現實質上的財富再分配。
總結
無條件基本收入,遠非一個「讓人不勞而獲」的懶人政策。它是一個應對21世紀社會結構性變遷——包括AI崛起、貧富擴大、勞動形式轉變——的宏大社會工程構想。全球各地的實驗數據打破了許多迷思,證明UBI在改善健康、教育、心理福祉與催化經濟活力上具有潛力,但其在財政可行性與政策設計上的巨大挑戰也同樣真實。基本收入者在實驗中的表現,也讓我們對工作倫理有更深刻的思考。
UBI的辯論,本質上是一場關於未來社會價值觀的對話:我們如何定義「工作」?我們是否承認生存本身就是一種權利?我們又該如何公平地分配由科技進步帶來的巨大紅利?
正如歷史所示,重大的社會福利改革,往往誕生於巨大的社會危機之時。或許,在AI全面衝擊就業市場的那一天到來之前,UBI都將停留在討論與小規模實驗的階段。然而,提前進行這場深刻的對話與探索,正是我們為一個更公平、更具社會整體韌性的未來,所能做的最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