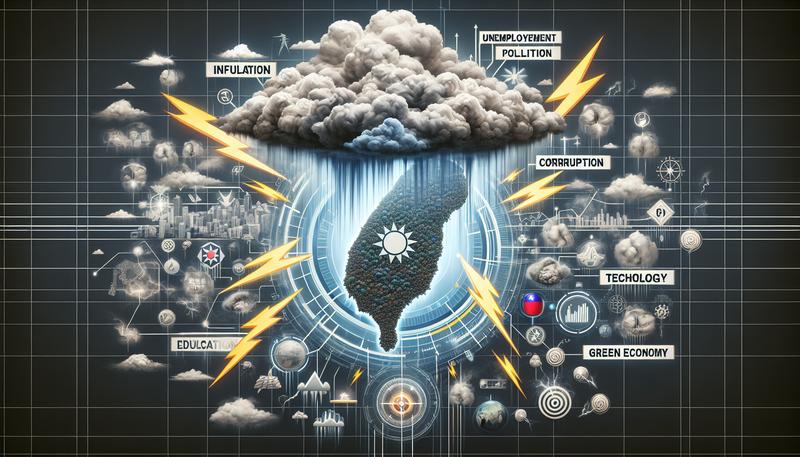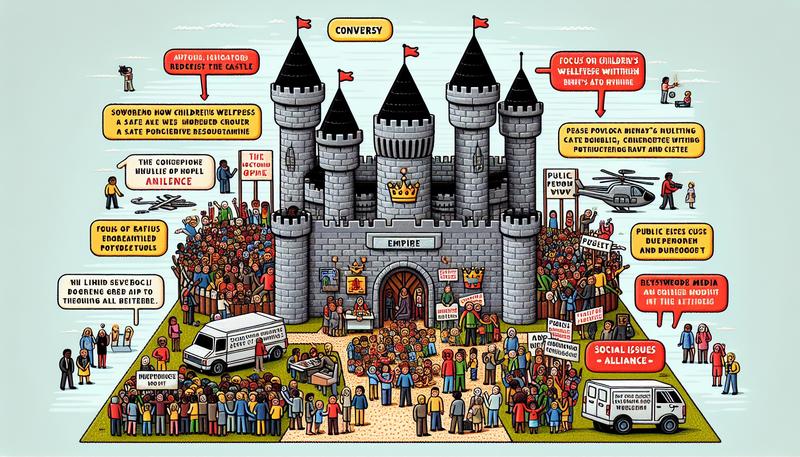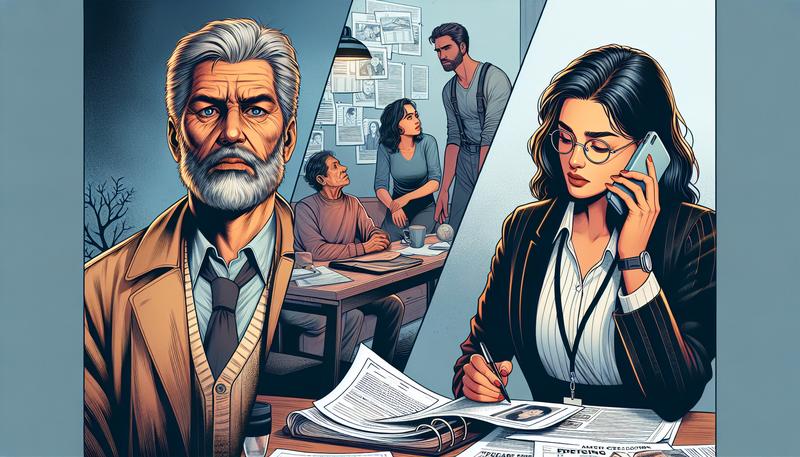「民粹主義」(Populism)無疑是當代全球政治的關鍵字。從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崛起、英國脫歐公投,到歐洲各國極右翼勢力的擴張,這股浪潮似乎重塑了世界政治地景。在臺灣,這個詞彙也從未在公共論述中缺席,的政治人物時常以「民粹誤國」來攻擊對手,網路論戰中也常見民眾互相指責對方「搞民粹」。然而,在一片標籤化的使用之外,我們是否真正理解這個複雜政治現象的意涵?
民粹主義究竟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一種動員策略,還是一種論述風格?它在不同國家有著哪些共通性與差異性?尤其在臺灣獨特的社會政治脈絡下,民粹主義呈現出何種「接地氣」的面貌?本文將整合多份學術研究與評論,深入剖析民粹主義的核心定義,並聚焦於臺灣的具體案例,探討民粹的測量方式、獨特之處,以及對民主體制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一、民粹主義的核心:純粹人民 vs. 腐敗精英
要理解民粹主義,必須先掌握其核心的政治邏輯。當代政治學界普遍認為,民粹主義並非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如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而是一種「中心思想薄弱的意識形態」(thin-centred ideology)。其核心觀念是將社會二元對立地劃分為兩個同質化的群體:「純潔、高尚的人民」(the pure people)與「腐敗、墮落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這個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末美國的農民運動,當時他們組成了人民黨(People’s Party)。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揚-沃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等學者的觀點,民粹主義者不僅僅是批評精英,他們更會宣稱自己是「唯一能夠代表真正的 人民」的聲音。在其政治語言的框架下,政治不再是多元利益的協商與妥協,而是一場道德鬥爭。任何反對其主張的個人、團體或制度,都會被打上「人民公敵」或「腐敗精英」的標籤,從而被剝奪其政治合法性。
民粹主義者追求實現一種所謂的「人民全意志」(general will),也就是一個由他們所定義的、至高無上的集體目標(例如「讓國家再次偉大」或「發大財」)。任何質疑或偏離此目標的聲音,都被視為對人民的背叛。其論述內容的核心,便是動員人民意志來對抗既有的政治秩序。因此,雖然民粹主義在表面上高舉「人民主權」,看似非常民主,但其本質上是「反多元主義」的。它否定了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承認社會由具有不同價值觀和利益的多元群體所構成,且這些群體都具有合法的存在權利。
二、測量台灣的民粹:一把多面向的尺
那麼,這個民粹主義的概念,該如何衡量一個社會或個人民粹主義的傾向程度?中央研究院與東吳大學的學者蔡明璋、潘欣欣透過實證研究,提出了觀察臺灣民粹主義的四個關鍵面向。這四個面向的強度,共同決定了民粹主義的傾向。
| 測量面向 | 核心信念與主張 |
|---|---|
| 1. 人民決策/主權在民 | 認為現行政治體制被精英把持,無法真正反映民意。他們相信政治並不複雜,應當由人民的意志直接引導政府決策。 |
| 2. 反精英主義 | 視政治精英、技術官僚與知識份子為一個脫離群眾、利益與人民相悖的同質化腐敗群體。他們所作所為都在「糟蹋人民」。 |
| 3. 人民的道德優越性 | 相信只有普通人(普羅大眾)才是真正誠心、老實的。由人民來做決定,才不會背離公共利益,才能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
| 4. 對強人領導的期盼 | 在公共政策方面,厭惡官僚體制中繁瑣的法規與程序,認為這會耽誤時機。他們渴望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者,能跳過體制障礙,立即實現人民的願望,這種期盼若推到極致,可能演變為對威權主義的嚮往。 |
根據這套測量標準,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存在相當普遍的民粹主義情緒。近八分之一的民眾有高度民粹傾向,而超過半數(54%)則屬於中度傾向。這意味著將近七成的臺灣民眾,對現有的政治精英與體制運作抱持著顯著的不滿。
此外,透過網路大數據分析也發現,在2018年至2021年間,「攻擊精英」的聲量在四個面向中遙遙領先,超過七百萬筆,遠高於「排斥他人」、「人民中心主義」和「擁戴共同理想」。這顯示「反精英」是臺灣民粹情緒中最主要、最響亮的元素。
三、接地氣的變貌:台灣民粹主義的四大特色
民粹主義在全球各地展現不同風貌,在臺灣,它也與在地的歷史與社會結構交織,呈現出四個顯著的特色:
1. 對貪腐的深刻不滿:
臺灣民眾普遍認為選舉耗費鉅資,而政治人物的資金來源不透明,使其與「貪污」、「賄賂」等形象緊密連結。這種觀感進一步延伸為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認為「法律遇到有錢有勢的人就會轉彎」,這種對政商勾結、權錢交易的深惡痛絕,成為民粹論述滋長的沃土。
2. 對年輕民主體制的信任危機:
臺灣的民主化歷程相對年輕,民主制度的根基尚未如歐美老牌民主國家般穩固。因此,當民眾對執政精英的信心低落時,這種不滿很容易從針對「個人」或「政黨」,擴散至對整個「民主制度」的質疑。諸如「民主有什麼好?都選一些不知道在幹嘛的人」這樣的怨言,正反映了這種對年輕民主體制的政治秩序可能構成侵蝕的潛在危機。
3. 矛盾的排他性—對同志與外來移民的態度:
研究發現,臺灣的民粹主義傾向與某種形式的本土主義及對同性戀、外來移民等群體的負面看法有關聯。這一點相當特殊,因為歐洲的排外民粹通常與大量的移民問題直接相關,而臺灣的移民比例極低,法規也相當嚴格。
此外,在一個相對世俗化、宗教影響力不像西方國家那麼大的社會,對同志議題產生強烈排斥,也顯示出臺灣民粹主義在社會層面的複雜性,其排他性根源並非完全能以西方理論解釋。
4. 缺乏左派政黨下的世代與階級焦慮:
臺灣民粹主義的支持者輪廓,呈現出年輕化、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從事不穩定工作的趨勢。在全球化與產業變遷下,這群年輕世代面臨著低薪、高房價、職涯發展不順遂的困境,內心積累了強烈的憤怒與受壓迫感。
然而,在臺灣的社會政治結構中,主流政黨中缺乏一個能穩定代表勞工階級、為其發聲的傳統左派政黨。這使得他們的經濟與階級焦慮,無法透過既有的政治管道有效疏導,其訴求也未能在福利政策上得到充分體現,因而特別容易被那些訴諸「打倒精英」、承諾提供簡單解方的民粹政治人物所吸引和動員。
四、誰是民粹主義者?台灣政壇的案例分析
在臺灣的政治語境中,政客之間常以「民粹」一詞當作攻擊他人的武器。然而,若回歸主流政治學術定義,誰更符合民粹主義者的形象?
典型的民粹主義者:韓國瑜
許多分析將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視為臺灣典型的民粹主義者。他的論述高度符合民粹主義的特徵:在競選大選期間,他將支持者稱為「偉大的高雄市民」或「庶民」,塑造出一個純潔的群體;同時,將當時由蔡英文總統領導的執政黨描繪成「權力中毒」、「無德無能」的腐敗權貴。
他將所有對他的批評都歸結為「精英的抹黑」與「政治奧步」。其核心訴求「高雄發大財」,尤其在後續的總統大選中,被塑造為一個不容質疑的集體意志,甚至為此提出「上任後禁止一切政治遊行」,因為「人民再也不想被意識形態綁架」。許多分析都認為,這種將社會簡化為「庶民vs.權貴」、並以單一經濟目標凌駕一切的論述,是民粹主義的典型展現。
菁英主義的反例:柯文哲與黃國昌
相較之下,有學者認為,柯文哲與黃國昌等人物,其本質更接近「菁英主義者」(Elitist),而非民粹主義者。菁英主義者同樣劃分群體,但他們尊崇的是擁有知識、能力、道德更優越的「政治菁英」(也就是他們自己),而將大眾視為需要被管理、甚至能力不足的「愚民」。
例如,柯文哲時常強調自己台大醫師的背景與高智商,並曾發表過「沒(經濟)產值的科系應該縮編」等言論,顯示其價值判斷傾向於以精英視角進行社會排序。黃國昌則以其學者背景與嚴謹的問政風格,同樣也帶有一種知識精英的形象。
他們雖然也猛烈批評政府,但其立足點更多是「我的專業能力比你強」,而非民粹主義者那種「我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姿態。他們與群眾的互動,更像是精英在號召民意來打擊政治對手,這是民主政治中精英為了爭取政權而競爭的常態,與民粹主義者自我矮化以融入人民的作法有所區別。
常見問題 (FAQ)
Q1: 民粹主義就等於民主嗎?
A: 不。這是最常見的誤解。民主的核心價值是「多元主義」,尊重並保障社會中不同聲音與少數群體的權利。民粹主義雖然也強調「人民作主」,但它通常是「反多元」的,它將「人民」定義為一個單一、同質的群體,並視任何反對者意見為不合法、需要被排除的「精英」或「敵人」。因此,民粹主義可以說是民主的黑暗面,而非民主本身。
Q2: 臺灣的民粹主義主要是左派還是右派?
A: 很難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光譜來簡單歸類。臺灣的民粹主義呈現出一種混合樣貌:它有類似左派的階級關懷(對經濟不公、階級流動停滯的不滿),但又缺乏清晰的左翼政黨來引導;同時,它也夾雜著右派的排他性與社會保守主義色彩(如對移民或同志議題的負面態度)。其核心驅動力更多是普遍的「反精英」、「反貪腐」情緒,而非特定的左右派經濟主張。
Q3: 為什麼年輕人、教育程度較低者更容易傾向民粹主義?
A: 根據研究,這主要與經濟因素和相對剝奪感有關。這些群體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可能面臨更大的生活壓力,如求職困難、薪資停滯、買不起房等。當他們感覺被整個體制拋棄,傳統的政治精英又無法回應其訴求時,就特別容易被那些言辭直接、姿態親民、承諾打破現狀的民粹型領袖所吸引。
Q4: 批評政府就是民粹嗎?
A: 不是。在民主國家,批評政府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監督制衡的必要環節。民粹主義是一種特定的論述風格和政治策略,它不僅僅是批評,而是將批評升級為一場「純潔人民」對抗「腐敗精英」的道德戰爭,並宣稱只有自己才能代表人民。因此,重點不在於「是否批評」,而在於「如何批評」以及批評背後的政治邏輯。
總結
綜合來看,臺灣的民粹主義並非單純複製歐美模式,而是在地政治文化、經濟結構與社會變遷下的獨特產物。它深刻反映了民眾對貪腐的厭惡、對政治精英的普遍不信任,以及特定世代與階級在全球化浪潮中所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研究顯示,儘管「反精英」聲量極高,但這種情緒似乎尚未普遍演變為徹底摧毀現有民主體制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力量。然而,其潛在風險不容忽視。韓國瑜式的民粹動員,已顯現出它如何侵蝕公共領域的理性思辨,將複雜的政策議題簡化為立場先行的標籤互鬥(如「1450 vs. 中共同路人」),這對民主的長期健康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
最終,應對民粹主義的挑戰,並非壓制不滿的聲音,或是將其輕易地標籤化。真正的解方,在於正視其背後的社會根源:經濟不平等、世代正義的失落、以及人民在政治過程中的疏離感。唯有透過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更透明的治理,以及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才能強化民主的韌性,引導這股沛然的民怨,從可能具破壞性的力量,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改革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