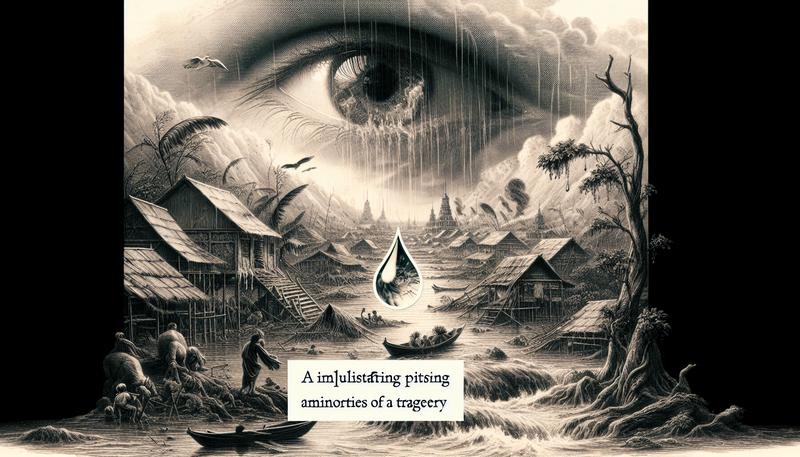在網路論壇如 PTT、Dcard 上,「仇女」一詞似乎已成為一種流行現象。從對女性外表的尖酸刻薄,到指責女性普遍拜金、崇洋媚外,乃至於「母豬教」等極端言論的出現,讓人們普遍認為「仇女」就是對女性的單純憎恨與厭惡。然而,若我們僅止於此種字面理解,將錯失其背後更為複雜且深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事實上,「仇女」(或在學術上更常被譯為「厭女」,Misogyny)並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情緒,它是深植於社會文化中的一種偏見與意識形態。女性主義與社會學家指出,厭女是父權體制(Patriarchy)賴以維繫其秩序的「執法機制」。它無所不在,不僅體現在男性的言行中,女性也可能在不自覺中內化並實踐這種價值觀。它的表現形式更是千變萬化,從赤裸裸的暴力,到偽裝成「關愛」與「保護」的微小侵犯(micro-aggression)。
本文章旨在深入剖析「厭女」的完整面貌,我們將從其定義出發,探討它在生活中各種顯性與隱性的表現形式,進而分析造成此一心態的深層原因與來源,並釐清其與「仇男」等概念的根本差異。唯有真正理解其運作邏輯與真相,我們才能跳脫情緒化的對立,共同挑戰這個束縛所有人的無形枷鎖。
重新定義「厭女」— 從字面到結構
要理解厭女,必須超越「討厭女人」的直觀印象,深入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與意涵。
詞源與普遍定義
「厭女」(Misogyny)一詞源於古希臘語,由 misos(仇恨)與 gunē(女性)組合而成。各大詞典普遍將其定義為「對女性的仇恨、蔑視、不喜或不信任」。然而,隨著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這個詞的內涵遠比字面意義更加豐富。例如,澳洲《麥考瑞詞典》便將其定義擴展至「根深蒂固的對女性的偏見」,突顯其系統性與文化性。
在中文語境中,「厭女症misogyny」或「仇女」成為網路常用語,而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的著作《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則讓「厭女」一詞在東亞社會引發廣泛討論。這些詞彙的流行,正反映了此一現象在當代社會的普遍性。
女性主義的視角:父權的執法者
康乃爾大學哲學家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其著作《不只是厭女》中,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她認為,將厭女簡單理解為「憎恨女性」是一種「天真的理解方式」,因為許多厭女行為的實踐者,可能在生活中深愛著特定的女性,例如他們的母親或妻子。
曼恩精準地區分了「性別歧視」(Sexism)與「厭女」(Misogyny):
- 性別歧視:是父權體制的理論與辯護部門。它負責創造並合理化男女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常以偽科學或傳統觀念包裝,例如主張「男性天生理性,適合領導;女性天生感性,適合照護」。
- 厭女:則是父權體制的警察與執法部門。它的核心功能並非仇恨,而是「控制並懲罰那些挑戰男性支配地位的女性」。這種厭女症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將女性劃分為「好女人」(順從、符合傳統角色)與「壞女人」(挑戰、反抗、不守本分),並對前者施以獎勵,對後者施以懲罰。
因此,當一位女性政治家因其強勢作風而遭受人格攻擊,或一位職業婦女因未將家庭置於首位而被批評為「自私」時,這些攻擊的根源往往並非出於對她個人的純粹厭惡,而是因為她們的行為「違反」了父權秩序所設定的女性角色,從而觸發了厭女這個「執法機制」。
社會學的觀點:一種文化態度
社會學家艾倫·G·約翰遜(Allan G. Johnson)將厭女定義為「一種因為女性的性別而仇視女性的文化態度」。他指出,厭女是性別歧視偏見與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男性主導社會中壓迫女性的重要基礎。其表現形式包羅萬象,從物化女性的色情作品、貶低女性的笑話,到家庭暴力,甚至引導女性對自己的身體產生厭惡感。
社會學家麥克·弗拉德(Michael Flood)則強調,厭女現象雖主要見於男性,但女性也可能對其他女性,甚至對自身施行厭女行為。這種「內化的厭女」使女性接受並認同社會對女性的貶抑,例如,熱衷於透過整形手術來迎合男性中心的審美標準,或是鄙視其他不符合傳統女性規範的女人。
無所不在的厭女—從顯性暴力到隱性控制
厭女的表現形式極為廣泛,它既可以明目張膽,也可以偽裝成溫情脈脈的關懷,使其更難以被察覺和反抗。
顯性的厭女表現
這是最容易識別的厭女形式,其核心是直接的敵意與攻擊。
| 表現形式 | 具體例子 |
|---|---|
| 針對女性的暴力 | 家庭暴力、性侵犯、伴侶謀殺,以及極端情況下的女性殺害(Femicide)。 |
| 言語攻擊與騷擾 | 網路上的仇女的言論(如PTT的「母豬教」)、職場或公共場合的性騷擾、對女性外貌或能力的公開貶損。 |
| 污名化與標籤化 | 創造並濫用「女司機」、「女博士」、「綠茶婊」、「黑木耳」等貶抑性詞彙,將特定羣體標籤化,以鞏固負面刻板印象。 |
| 歷史與文化敘事 |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視女性為「不完整的男性」;中國古代的「紅顏禍水」論,將王朝覆滅歸咎於女性。 |
隱性的厭女表現:「仁慈的性別歧視」
這是厭女最狡猾、也最普遍的形式。它披著「善意」與「保護」的外衣,看似在幫助女性,實則將女性置於次等、被動、需要被支配的地位,從而鞏固不平等的權力結構。
「霸道總裁」的迷思與騎士精神
電影或影視作品中流行的「霸道總裁」角色,以及現實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內」、「男人就該保護女人」等論述,是典型的仁慈性別歧視。這些言行看似體貼,其潛台詞卻是:「女性是柔弱的、無能的,需要男性的經濟支持與決策引導」。當男性堅持支付所有約會開銷、不讓女性從事「辛苦」的工作、或替女性做決定時,他們正是在實踐一種溫和的控制,剝奪了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性。
性物化與雙重標準
厭女文化將女性的身體視為滿足男性慾望的客體。這導致了嚴重的性別雙重標準:的男人性經驗豐富被視為有魅力的象徵,而女性若展現性自主則可能被貼上「蕩婦」、「不檢點」的標籤。佛洛伊德提出的「聖母-妓女情結」正是此現象的深刻描繪:男性將女性二分為值得尊重但無性的「聖母」(如母親、妻子)和可以引發慾望但備受鄙視的「妓女」。這種割裂使女性的性慾無法被正當看待。
對「女性化」特質的貶低
厭女不僅針對生理女性,更擴及所有被視為「女性化」的特質、行為或羣體。
- 恐同(Homophobia):對男同性戀者的厭惡,常與厭女交織。許多恐同言論會以「娘娘腔」、「女裏女氣」等詞語攻擊男同性戀者,其背後邏輯是:將男性「女性化」是一種貶低,因為「女性」本身就是次等的。
- 恐女氣質症(Femmephobia):學者蕾亞·阿什莉·霍斯金(Rhea Ashley Hoskin)提出此概念,指對展現女性氣質的壓迫,無論實踐者是何種性別。
- 職業與興趣的價值排序:被認為充滿「陽剛」特質的職業(如工程師、外科醫生)往往比充滿「陰柔」特質的職業(如護理師、幼教老師)獲得更高的社會評價與薪資,這也反映了深層的厭女價值觀。
女性的厭女情結
生活在厭女文化中的女性,也難免會將這套價值觀內化。當女性認同「男性更優越」的觀念時,便可能產生對自身或其他女性的厭惡。
- 自我貶抑:例如,女性自稱「女漢子」並引以為傲,潛意識中是認同「漢子」(男性)的特質優於傳統女性特質。或是在遭遇挫折時感嘆「做女人真倒楣,下輩子想當男人」。
- 為難女性:在家庭或職場中,部分女性會主動扮演父權秩序的代理人。比方說,婆婆用傳統媳婦的標準要求兒媳,或女性主管對女下屬抱持更嚴苛的偏見,認為「女人就是情緒化、難管理」。她們透過與「壞女人」劃清界線,來換取在父權體制下的安全感與認同。
仇女心態的成因—無力感的投射與社會壓力
厭女心態的形成,並非單純出於邪惡,它往往是個人在社會結構性壓力下,無力感與挫敗感扭曲後的產物。
社會結構的雙重束縛
父權體制在給予男性羣體「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的同時,也對男性施加了沉重的枷鎖。社會期望男性必須扮演「成功者」與「供養者」的角色,要求他們在事業、財富上取得成就,並承擔起成家立業的主要責任。
男性的挫敗感與怨恨轉移
當男性會在現實中無法達到社會設定的「成功」標準時,便容易產生強烈的挫敗感與焦慮。
- 經濟壓力與相對剝奪感:許多男性將買房、買車視為成家的必要條件,背負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他們的經濟能力與對錢的看法,深刻影響其人生觀。當他們看到女性倡導「旅行找自己」、追求生活品質時,容易產生「那是因為妳們不用負責養家」的怨恨。這種怨恨並非針對女性個人,而是對自身所處困境的無力反抗。
- 求偶焦慮與歸因謬誤:在男女關係中遭遇挫折的男性,特別是那些自認善良、努力卻追不到妹的人,很容易將失敗簡單歸因於「女人都愛錢」、「女人只看臉」。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讓他們無需痛苦地檢討自身在個性、溝通、魅力等方面的不足,而是選擇一個簡單的外部敵人——「膚淺的女性羣體」——來發洩自己的無能為力,把問題怪到別人身上。如作家御姊愛的文中所觀察,這些仇女言論背後,往往是「對社會現狀與性別期待的無力抵抗」。
理想破滅與仇恨生成
許多男生在成長過程中,被灌輸了「只要真心付出,就能獲得美好愛情」的浪漫童話。然而,當他們在現實中遭遇背叛、情感勒索,或發現對方的行為極度自私,甚至遇到所謂的渣男搶走心儀對象時,這種理想的破滅會帶來巨大的心理衝擊。他們無法理解為何自己的「善意」與「努力」換不來預期的回報,巨大的失望最終可能轉化為對整個女性羣體的 cynicism(憤世嫉俗)與仇恨。
網路社羣的同溫層效應
PTT 等網路論壇的匿名性,為這些帶有挫敗感與怨恨的男性提供了一個情緒宣洩的出口與同溫層。在羣體中,個人的不滿被放大、被共鳴、被正當化,這類極端的「仇女」言論得以迅速傳播並凝聚成一種集體認同(如「母豬教」)。這使得原本可能只是個人層面的負面情緒,升級為一種具有攻擊性的次文化,許多朋友之間也可能互相影響。
釐清相似概念—厭女 vs. 仇男
在討論厭女時,常有人提出「仇男」(Misandry)也應受到同等批判。要釐清此問題,我們必須回到結構性的視角。
何謂「仇男」?
從個人層面看,對男性的偏見、歧視或仇恨當然存在。而在女性主義的框架下,「仇男」也可以被理解為父權體制對男性的懲罰機制:當男性未能符合「陽剛」的性別規範時(例如,表現出脆弱、情感豐富,或選擇成為家庭主夫),他們同樣會遭受來自社會的嘲笑與排斥。
結構性的不對等
然而,「厭女」與「仇男」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厭女是存在於一個名為「父權制」的、系統性的社會結構之中,而「仇男」則缺乏這樣的結構性支持。
正如專欄作家空心二胡所做的思想實驗,一個真正「仇男」的社會將會是:
- 男性的價值完全由女性定義,其主要功能是取悅女性。
- 男性被要求事業成功,但又會因此被批評為「充滿心機」,影響其社會地位。
- 整個社會的文化、法律、經濟體系都以女性為中心來設計,系統性地忽視或貶抑男性的需求與經驗。
顯然,我們的現實世界並非如此運作。目前並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由女性支配的「母權制」(Matriarchy),能夠系統性地壓迫男性。因此,雖然針對男性的個人偏見存在,但將「仇男」與「厭女」視為對等的、可相互抵銷的現象,是忽略了兩者背後巨大的權力結構差異。
常見問題 (FAQ)
Q1: 喜歡女生、有女性親友的男性,還會是「厭女」嗎?
A: 會的。如哲學家凱特·曼恩所言,厭女的核心是「控制與懲罰」,而非「普遍的仇恨」。一個男性可以深愛他的母親、妻子或女性朋友,因為她們符合他心中「好女人」的角色,但同時對一位挑戰男性權威的女性政治人物或女上司抱持強烈敵意。他愛的是「遵守規則的女性」,而懲罰的是「破壞規則的女性」。
Q2: 女性主義者是不是都在「仇男」?
A: 不是。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解。女性主義批判的是「父權體制」這個壓迫性的社會結構,而非「男性」這個生理羣體。父權體制同樣透過僵化的性別角色(如男性必須堅強、不能示弱)來傷害男性。女性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解放所有人,讓每個人都能擺脫性別的束縛。
Q3: 如果我真心覺得某些女性的行為很有問題,這也算「厭女」嗎?
A: 這取決於您批評的框架。批評一個個體的負面行為本身是正常的。但如果您的批評符合以下幾點,則可能帶有厭女色彩:(1) 過度概化:將個體行為上升到對整個女性羣體的攻擊(例如,「台女不意外」);(2) 使用性別羞辱:使用針對女性的侮辱性詞彙;(3) 基於性別角色的雙重標準:認為某件事是錯的,僅僅因為實踐者是「一個不該這麼做的女人」(例如,批評女性「太有野心」)。
Q4: 台灣的女性地位已經很高了(例如曾有女總統),為什麼還需要討論「厭女」?
A: 法律與政治層面的形式平等,不完全等同於文化與社會層面的實質平等。雖然台灣在性別平權上成就斐然,但厭女文化仍深植於社會的許多角落。例如:網路空間中普遍存在的仇女言論、媒體對女性政治人物不成比例的私生活關注、職場中對懷孕女性的隱性歧視、以及家庭內部極不平等的家務勞動分配。這些都證明瞭父權結構及其厭女的執法機制依然在運作中,挑戰它們仍然至關重要。
總結
厭女,遠非「討厭女人」這麼簡單。它是一套複雜、隱蔽且強大的社會運作機制,是父權秩序的忠誠衛兵。它透過獎勵順從、懲罰反抗的方式,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設定好性別的腳本,任何試圖脫稿演出的人,都可能成為它攻擊的目標。
無論男女,我們都生活在這個結構之中,既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在不自覺中成為加害者。男性因無法達成社會的陽剛期待而產生的挫敗與無力感,進而轉化為對女性的怨恨;女性則可能內化了這套貶抑自身的價值觀,轉而用它來審判自己與他人。
理解厭女的真正意涵,並非為了挑起性別對立或指責任何個人,而是為了揭示這個傷害所有人的系統性問題。唯有看清它的運作邏輯,我們才能開始有意識地挑戰它:在日常生活中辨識並拒絕那些「仁慈的性別歧視」,停止使用貶抑任何性別的標籤,並對那些源於挫敗感的仇恨言論多一分結構性的理解,而非僅僅回以情緒化的反擊。
最終,拆除父權體制及其厭女的執法機制,不是要建立一個「女尊男卑」的新世界,而是要創造一個真正尊重個體差異、讓所有人——無論其性別為何——都能自由、完整地成為自己的社會。這條路漫長而艱鉅,但深刻的理解,永遠是改變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