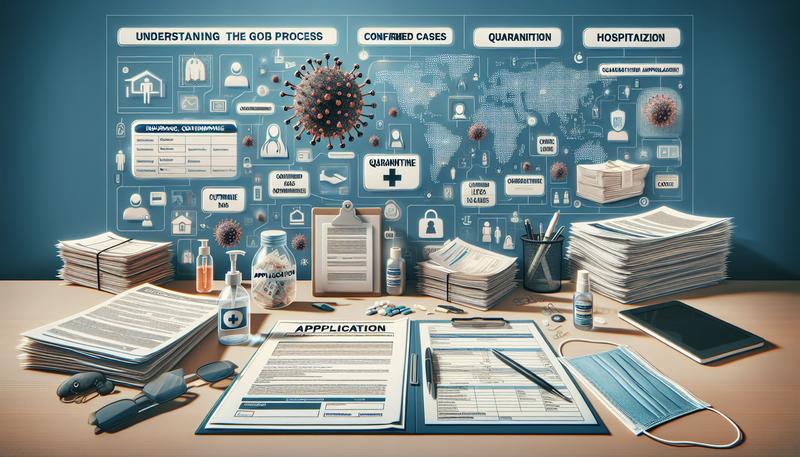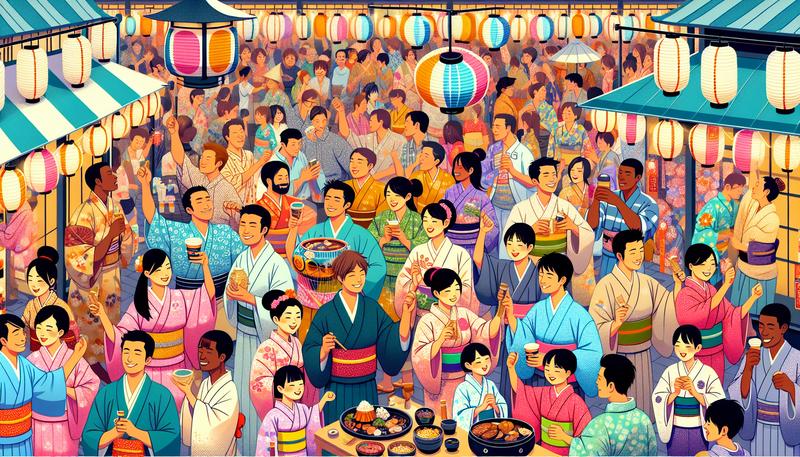「我們所看到的,都已經是倖存下來的孩子了。那些活不過 5 歲成年禮,被各種未經消毒過的器具,不管是玻璃、指甲,甚至是石頭所蹂躪的女孩們,因為疼痛、感染,甚至出血而永遠無法長大的小女孩們,你是不可能有機會看得到的⋯⋯」根據一位記者的採訪,一位在索馬利蘭行醫的台灣作者,道出了這個議題最沉痛的核心。這種被稱為「女性割禮」(Female Circumcision)或更準確地說是「女陰殘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的陋习,是一道刻在全球超過兩億名女性身上的深刻烙印。
這項割礼習俗並非僅存於遙遠的非洲部落,它也悄然存在於新加坡等現代化國家,並隨著移民社群擴散至歐美。它被包裹在「傳統文化」、「純潔」與「宗教」的外衣之下,實則是對女性的一種身體與人權的極端暴力。它是一個複雜的議題,牽涉文化、社會規範、性別權力與公共衛生。本文章將深入剖析女陰殘割的定義與類型、全球的盛行狀況、其背後盤根錯節的動機、對女性健康造成的無法抹滅的傷害,以及全球為終結此陋习所付出的努力與面臨的挑戰。
何謂女性割禮?定義、類型與執行方式
世界衛生組織的明確定義
世衛組織(WHO)對女陰殘割的定義是:「包括所有涉及為非醫學原因,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生殖器,或對女性生殖器造成其它傷害的程序。」此定義的關鍵在於「非醫學原因」,明確指出這項陋習的操作程序沒有任何健康上的益處,純然是一種傷害。
殘割的四種類型
女性割禮的執行方式因地区與族群而異,世衛組織將其大致歸納為四種主要類型:
第一型 (Type I):陰蒂切除術 (Clitoridectomy)
- Ia 型:僅切除陰蒂的包皮。
- Ib 型:部份或全部切除陰蒂。這是較常見的形式,施行者會用手指將陰蒂捏住拉出,再用尖銳物體將其割下。經歷此手術的女性,其外陰部在視覺上變得「光光的」,失去了原有的生理結構。
第二型 (Type II):切除術 (Excision)
- IIa 型:僅切除小陰唇。
- IIb 型:部份或全部切除陰蒂及小陰唇。
- IIc 型:部份或全部切除陰蒂、小陰唇及大陰唇。
第三型 (Type III):鎖陰術 (Infibulation)
這是最極端且傷害性最強的類型,又稱為「法老式割禮」。此手術會切除部份或全部外生殖器(陰蒂、小陰唇、大陰唇),然後將傷口兩側縫合,僅在陰道口留下一個約 2-3 毫米的微小小孔,供尿液與經血排出。為了幫助傷口癒合,女孩的雙腿會被緊緊綑綁長達數週。
直到婚後,這個開口才由丈夫用陰莖強行頂破,或由助產士用刀割開,過程極度痛苦。女性每次生產後,可能還會經歷「再縫合手術」(Reinfibulation),重新縮小陰道口。此类型主要集中在非洲東北部的索馬利亞、蘇丹、吉布地等國家。
第四型 (Type IV):其他所有有害程序
此類型涵蓋所有其他非醫療目的、傷害女性生殖器官的行為,例如:穿刺、燒灼、刮除、切割陰道組織(如奈及利亞的吉西里切割),或是在陰道內放入腐蝕性物質或植物以造成緊縮感。
野蠻的執行方式
施行者通常是村落中的年長女性、傳統接生婆,甚至是理髮師,但也有部份地區(如埃及)已出現「醫療化」趨勢,由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執行。然而,在多數地區的情况下,執行過程極其簡陋且危險:
- 工具:使用未經消毒的刀片、剪刀、碎玻璃、磨利的石頭,甚至是操作程序執行者的指甲。
- 環境:通常在家中或衛生條件惡劣的地方行割禮。
- 麻醉:絕大多數情況下不使用任何麻醉,女孩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承受劇痛。
全球分佈與驚人數據
女陰殘割的地理分佈高度集中,主要位於非洲從西岸的塞內加爾到東岸的索馬利亞,並向南北延伸的廣大地區,以及中東(如葉門、伊拉克庫德族地區)和亞洲部份地區(如印尼)。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數據,全球至少有 2 億名女性經歷過此程序,且每年仍有超過 400 萬名女孩面臨割禮的風險。
各國女性割禮盛行率 (15-49歲女性)
以下表格根據 UNICEF 2016 年的數據,顯示了部份國家驚人的盛行率:
| 國家 | 盛行率 (15-49歲) |
|---|---|
| 索馬利亞 | 98% |
| 幾內亞 | 97% |
| 吉布地 | 93% |
| 獅子山 | 90% |
| 馬利共和國 | 89% |
| 埃及 | 87% |
| 蘇丹共和國 | 87% |
| 厄利垂亞 | 83% |
| 布吉納法索 | 76% |
| 甘比亞 | 75% |
| 衣索比亞 | 74% |
| 奈及利亞 | 25% |
| 肯亞 | 21% |
| 葉門 | 19% |
| 伊拉克 | 8% |
各國女童割禮盛行率 (0-14歲)
這項數據反映了割礼陋習是否仍在延續。雖然許多國家的比率有所下降,但在部份地區依然嚴峻。
| 國家 | 盛行率 (0-14歲) |
|---|---|
| 甘比亞 | 56% |
| 茅利塔尼亞 | 54% |
| 印度尼西亞 (0-11歲) | 49% |
| 幾內亞 | 46% |
| 厄利垂亞 | 33% |
| 蘇丹共和國 | 32% |
| 埃及 | 14% |
| 奈及利亞 | 17% |
| 葉門 | 15% |
| 肯亞 | 3% |
不僅限於非洲與中東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割禮這種情況並非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在已開發國家新加坡,此習俗仍存在於部份的馬來穆斯林社區中。他們通常在女嬰出生後不久進行,形式較輕微,但其背後反映的性別控制與剝奪身體自主權的意涵並無二致。隨著全球移民的流動,在歐洲、北美、澳洲等地,也出現了來自實踐割禮文化背景的移民家庭為女兒秘密進行手術的案例。
盤根錯節的動機:為何延續千年?
一項帶來如此劇痛與傷害的割禮習俗,為何能延續至今?其原因錯綜複雜,絕非單一因素可以解釋。
強大的社會規範與認同感
這是最主要且最強大的驅動力。在實行割禮的社區中,這被視為女孩轉變為女人的成年禮,是成為「真正女人」的必要條件。未經割禮的女孩會被視為「不潔」、「不端莊」,遭受社會排斥、嘲笑與羞辱,難以找到結婚對象。一位母親沉痛地說:「要成為一位真正的女人就要『切』,如果不切是會被虐待和辱罵的。」為了讓女兒能順利融入社區、獲得婚姻的保障,父母(尤其是母親)不得不讓女兒承受這一切膚之痛,這是傳統文化中非常悲哀的一面。
對女性的性控制
許多文化相信,割禮能降低女性的性慾,從而確保她們在婚前保持貞潔,婚後對丈夫忠誠。這種觀念將女性的身體視為需要被控制的對象,其性的表達被認為是危險的、需要被抑制的。
錯誤的宗教連結
儘管《古蘭經》與《聖經》中均未提及女陰殘割,也與猶太教無關,許多人仍誤以為這是宗教的要求。在馬利、幾內亞和埃及等國,這種觀念尤為普遍。事實上,此習俗的起源早於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但後來與伊斯蘭文化中對女性貞潔的要求相結合,而被錯誤地賦予了宗教意涵。許多伊斯蘭教最高權威機構,如埃及的艾資哈爾大學,已公開聲明女陰殘割與伊斯蘭教法無關,並予以譴責。
衛生與美學的扭曲觀念
部份社群認為女性的外生殖器是「醜陋」且「不潔」的,切除後會更乾淨、更美觀。這種觀念將自然的生理結構病態化,反映了對女性身體的極端物化。
女性的支持與執行
這是一個令人心痛卻又無法迴避的事實:女性割禮的執行者與傳承者,往往是女性自己——母親、祖母、姑姨等。她們身為過來人,深知其痛苦,卻也深知不這麼做的社會後果。在這種結構性的壓力下,她們成為了維繫這項傳統文化的共犯,將自己曾經的創傷,複製到下一代女性身上。
無法抹滅的傷害:身心併發症
女性割禮對女性健康構成全面且終身的威脅。許多記者與攝影師,如 Stephanie Sinclair,透過影像記錄了這些對女性的傷害,其作品深刻揭示了割禮對女性健康造成的悲劇。
短期併發症
- 劇烈疼痛與休克:在無麻醉的情況下,劇痛可能導致神經性休克。
- 大出血:切斷陰蒂動脈可能導致無法控制的出血,甚至死亡。
- 感染:使用不潔工具極易引發傷口感染、破傷風、敗血症,甚至傳播 B 型肝炎、C 型肝炎及 HIV。
- 排尿問題:術後腫脹與疼痛會導致尿滯留。
- 死亡:許多女孩因上述併發症而夭折,成為無法被看見的統計黑數。
長期併發症
- 慢性感染:反覆的泌尿道與骨盆腔感染。
- 排尿與經期問題:傷口癒合後形成的疤痕組織,特別是「鎖陰術」,會嚴重阻礙尿液與經血的排出,導致排尿困難、滴尿、經痛,甚至經血倒流形成子宮積血。
- 性功能障礙:疤痕組織導致性交疼痛,而陰蒂的切除更直接剝奪了女性最主要的性快感來源,導致性慾低下、性冷感。
- 生育併發症:疤痕組織會影響產道擴張,導致難產、產程遲滯、會陰嚴重撕裂。WHO 的研究指出,經歷過割禮的女性,其新生兒死亡風險顯著高於未受割禮者,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 10 至 20 名的死亡可歸因於母親曾遭受割禮。
- 心理創傷:經歷割禮的女性普遍承受著長期的心理創傷,包括焦慮、憂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她們可能會感到被家人背叛、身體不完整,產生深刻的恥辱感。
歷史的軌跡與反對的浪潮
歷史溯源
女性割禮的確切起源已難以考證,但其歷史悠久。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西元前 25 年的著作中,就曾描述過古埃及人有為女性行割禮的習俗。然而,諷刺的是,在 19 世紀,部份西方人也曾將切除陰蒂視為一種「醫療手段」,用來「治療」女性的自慰、歇斯底里、癲癇等所謂的「精神疾病」,這段歷史揭示了對女性身體的控制與污名化,並非僅是「非西方」的專利。
反對運動的興起
- 早期反抗:20 世紀初,在肯亞的基督教傳教士率先反對此習俗,卻也引發了當地基庫尤人為維護傳統文化而發起的激烈抵抗。
- 非洲女權的覺醒:1970 年代,以埃及醫師納瓦勒·薩達維(Nawal El Saadawi)為代表的非洲女權主義作者,勇敢地站出來批判此習俗,將其定義為對女性的壓迫。
- 國際社會的介入:自 1990 年代起,聯合國將女陰殘割正式定義為對人權的侵犯。WHO、UNICEF 等機構投入大量資源,與 Tostan、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等非政府組織合作,透過社區教育、法律倡議等方式,推動廢除此習俗。2012 年,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決議,呼籲全球致力消除女陰殘割。
法律的進展與挑戰
目前,絕大多數實行陋習的國家以及歐美國家都已立法禁止女性割禮這項操作程序。然而,法律的執行往往力不從心。由於手術多為秘密進行,舉證困難,定罪案例寥寥可數。更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出現了反撲的聲浪。例如,2024 年,西非國家甘比亞的國會竟高票通過一項意圖撤銷割禮禁令的法案,若最終通過,將成為全球首個開倒車的國家,顯示這場終結陋習的戰役的艱鉅性。
複雜的論述:文化相對、人權與性別
面對女陰殘割,國際社會也存在著複雜的論述辯證。
文化相對主義 vs. 普世人權:
部份人類學家與後殖民學者批評,西方人主導的反割礼運動帶有「文化帝國主義」色彩,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於非洲文化之上。他們認為,應尊重在地文化的多樣性。然而,反對者主張,文化不應成為侵犯基本人權(如健康權、免於酷刑的權利、身體自主權)的藉口,尤其是對女孩人權的侵害。當一項「傳統文化」對特定群體(尤其是無力反抗的兒童)造成明確且嚴重的傷害時,人權的普世性應優先於文化的相對性。
與男性割包皮及醫美手術的比較:
有人質疑,為何社會強烈反對女性割禮,卻普遍接受男性割包皮(犹太教等宗教有此要求)?或是將其與削骨、隆乳等醫美手術類比。對此,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指出關鍵差異在於:
- 同意權:女性割禮的受害者絕大多數是未成年女童,在被暴力脅迫下完成,完全沒有同意權。
- 傷害程度:女性割禮對身體造成的傷害與健康風險,遠遠超過男性割包皮或常規的醫美手術。
- 背後意涵:女性割禮的核心是控制女性的性與身體,而男性割礼或醫美手術的社會意涵則相對複雜,但女性割禮的壓迫性更為直接與赤裸,它是對女性的一種根本性控制。
核心問題:
身體自主權與性別不平等:剝開文化、宗教、傳統文化的層層外衣,女陰殘割的核心,是一個根植於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規訓與控制女性的身體,使其符合社會對「理想女性」的狹隘定義。因此,終結割礼的根本之道,不僅是禁止手術本身,更是要挑戰其背後不平等的權力結構。
常見問題 (FAQ)
Q1: 女性割禮和宗教有關嗎?
A: 整體而言沒有直接關聯。這是一項早於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文化習俗。儘管在某些地區被錯誤地與宗教掛鉤,但沒有任何主要宗教的教義要求或支持女性割禮。許多宗教領袖已公開譴責此行為。
Q2: 為什麼女性會支持並為自己的女兒施行割禮?
A: 這是出於極大的社會壓力與一種扭曲的保護心態。在實行割禮的社區中,母親們相信這是確保女兒能夠被社會接納、成功嫁人、維護家族榮譽的唯一途徑。她們是結構性壓力的受害者,同時也成為了這項傳統文化的傳遞者。
Q3: 女性割禮和男性割包皮一樣嗎?
A: 不一樣。儘管兩者都涉及生殖器的切割且在未成年人身上進行時都涉及同意權問題,但存在根本差異:
- 1. 健康影響:女性割禮沒有任何健康益處,且會導致嚴重的短期與長期併發症,嚴重影響女性健康。男性割包皮的健康影響則存在一些醫學爭議,但普遍認為其傷害性遠低於女性割禮。
- 2. 傷害程度:女性割禮的類型(尤其是第三型)涉及大量組織的切除與缝合,傷害極大。男性割包皮僅切除包皮,是相對簡單的手術。
- 3. 目的:女性割禮的主要社會功能是控制女性的性自主,而男性割禮的動機則更多元,包含宗教、文化及衛生等。
Q4: 女性割禮在全球是合法的嗎?
A: 在絕大多數國家,包括那些盛行此陋習的非洲國家,女性割禮都是非法的。然而,由於其深植於文化中,法律的執行非常困難,秘密進行的案例依然猖獗。令人擔憂的是,部份地區甚至出現了試圖將其合法化的政治動向。
Q5: 我們可以如何幫助終結女性割禮?
A: 個人可以透過多種方式提供幫助:
- 1. 教育與傳播:分享正確資訊,讓更多人了解女陰殘割的真相與危害。
- 2. 支持專業組織:捐款支持在第一線工作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人口基金、UNICEF、國際培幼會)與在地非政府組織。
- 3. 倡議:關注相關議題,支持各國政府制定並嚴格執行禁止女性割禮的法律,並為受害者提供庇護與援助。
- 4. 促進性別平等教育:從根本上支持並推廣性別平等的觀念,挑戰所有形式的性別暴力。
總結
女陰殘割是一項野蠻且殘酷的習俗,它以傳統文化為名,行暴力之實,對全球數以億計的女性造成了終身的、無法逆轉的身心創傷。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健康議題,而是一個深刻的性別議題與人權議題,尤其侵害了女孩人權。
儘管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努力已使割禮盛行率緩步下降,但這場戰役遠未結束。法律的頒布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改變來自於教育的普及、女性的賦權,以及從社區內部發起的觀念轉變。我們需要讓更多人了解,割禮並非榮耀的象徵,而是痛苦的根源;女性的身體不屬於任何人,只屬於她自己。
如同那位在非洲行醫的台灣醫師所期許的,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專業的介入,更是一份「有溫度的同理」。唯有溫柔而堅定地與在地社區站在一起,支持那些勇敢反抗的女性,拆解那盤根錯節的壓迫性結構,我們才能真正期望,在未來的某一天,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女孩,需要用自己的身體,去承受如此沉重的文化烙印。